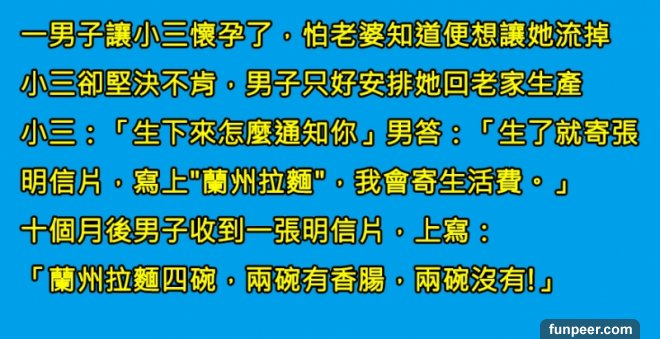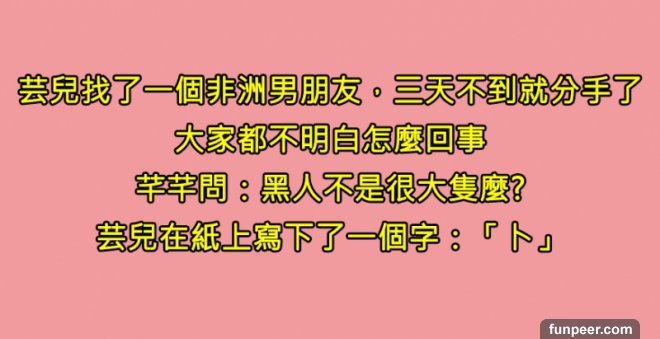《到頭來,我們擁有的一切,只有文字》── 瑞蒙.卡佛談寫作
叫我自己親愛的── 瑞蒙.卡佛談寫作》 到頭來,我們擁有的一切,只有文字。 美國最偉大的 短篇小說家瑞蒙‧卡佛 寫給未來創作者的傳世之書! 33篇從未集結出版之作,繁體中文版首度問世。 專文導讀◎陳榮彬(臺大翻譯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如果作家不能心口如一的寫出內心想法,拜託,快點轉行。」 ──瑞蒙.卡佛 為何卡佛從不寫長篇小說? 誰是將卡佛領進文學窄門的導師? 誰是他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推手? 卡佛心目中的好作品,標準為何? 卡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言有哪些? 卡佛出身寒微,十九歲即奉子成婚。接下來的數十年人生裡,他為了一家四口的生計奔忙,屢屢跌入困境,乃至最終亦步上父親後塵,成了酗酒之徒。然而,即便在最困頓時,卡佛對文學的熱愛仍堅持不變,他從二十歲起開始寫作,接下來的二十年,寫作成了他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出口。1983年,他獲得「米德瑞暨哈洛.史特勞斯生活年金獎」,才從經濟窘境中徹底解脫,五年後便因病過世,然而他在短篇小說所奠定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出其右。 -- 一個平凡真誠的「說故事的人」 -陳榮彬(臺大翻譯碩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任何人的生平若能夠真誠地被述說出來,都可以成一本小說。」 ——引自海明威《死在午後》(Death in the Afternoon) 【為小人物說話】 一九九三年,好萊塢大導演羅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已於二○○六年去世)拍了一部叫做 Short Cuts 的電影,雖然莫名其妙地被台灣片商翻譯成《銀色.性.男女》(可以看到小勞勃.道尼成為「鋼鐵人」之前的青澀模樣!),但從原文不難了解那是一部由許多故事湊起來的電影,而且阿特曼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當代美國短篇小說名家瑞蒙.卡佛。隔年,時報出版社翻譯出了阿特曼為這電影編的一本卡佛故事集,書名還是叫做 Short Cuts ,中譯本受電影影響,取名為《浮世男女》(已絕版)。把這本故事集中譯本翻開一看,我就手不釋卷了,內心納悶卡佛為什麼可以把那些小人物寫得那麼絕?無論是〈鄰居〉裏面那一對幫鄰居照顧房子的無趣夫妻,或是〈他們不是妳的丈夫〉裏面失業的魯蛇丈夫,還有〈告訴那些娘兒們我們去了〉那兩個一起犯下性暴力重罪的好朋友,都被寫得如此真實。我想,描寫平凡的人生,也是一種本事吧?而且最重要的理由,應該是他自己也經歷過,且看他在本書的〈火〉裏面細數自己做過哪些瑣碎的零工:「在鋸木廠待過,也當過大樓管理員,送貨員,在加油站打工,在庫房打掃……只要說得出的,我都幹過。有一年夏天,在加州的阿克塔 —— 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為了養家活口,白天的時間都在採鬱金香;晚上在餐館打烊之後,我還到一間得來速餐廳做內勤和清理停車場的工作。有一次我甚至考慮應徵收帳員……」。卡佛在這本書裏面,雖然並不是很有系統的,但多少也交代出自己的生平與他短篇小說書寫之關係,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談寫作〉 回顧一九六○年代中期,我發現我對於長篇小說有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困擾。有一陣子不管是讀是寫都有困難。我的注意力持續度節節敗退;我完全沒了寫小說的耐心。現在想起來都還是一段冗長而沉悶的經歷。不過我明白,這段過去跟我現在愛寫詩和短篇小說大有關係。直切,直入,不拖泥帶水,毫不遲疑。大概也就在同一時期,在我二十五歲以後的這段時間裏,我失去了強烈的企圖心 ── 若真如此,倒也是好事一樁。企圖心加上一點點的運氣,對於一個有心寫作的人來說是好事。若是企圖心太大加上運氣不好,或者連一點運氣也沒有,那是會要人命的。寫作必須有天分。 有些作家非常有天分;作家應該都有天分吧。但是要擁有看待事物的獨特性和敏銳度,而且能精準貼切的表達出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蓋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當然是作者約翰.厄文(John Irving)心目中最精採的世界。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寫的則是她眼中的世界;另外,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們的世界。契佛(John Cheever)、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以撒.辛格(Isaac Singer)、斯坦利.艾肯(Stanley Elkin)、安.比提(Ann Beattie)、辛西亞.奧茲克(Cynthia Ozick)、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註: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美國後現代主義小說家,重要作品有《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等。得獎無數,被譽為「今日眾多年輕作家的文學教父」。)、瑪莉.羅比森(Mary Robison)、威廉.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貝瑞.漢納(Barry Hannah)、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也各自有他們心中的世界。每一位偉大的或是出色的作家,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造就屬於他的世界。 我上面所說的,其實有些類似「風格」,但風格不是一切。作家在他書寫的每件事物上都簽了字,具有他獨一無二、絕不會錯認的署名。那是他的世界,絕對不會是其他人的。這是造就作家的要件之一,而非天分。有天分的人比比皆是。但一個作家有獨特的見解,而且能夠把見解信達雅的訴諸文字:那麼這個作家就會有一席之地。 伊薩克.狄尼森(註:Baronesse Karen Von Blixen-Finecke,1885-1962,丹麥作家,以英語寫作,伊薩克.狄尼森(Isak Dinesen)為其筆名,其生平曾拍成電影《遠離非洲》。)說她每天都會寫一點東西,沒有指望也沒有絕望。將來我會把這句話記在名片大小的卡片上,貼在我書桌旁的牆壁上。牆壁上現在已經貼了幾張這類3×5的小卡片。其中一張寫着:「敘事基本的精確度是寫作第一也是『唯一』的道德。」是艾茲拉.龐德(註:Ezra 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文學家。)說的。精確「當然」不是一切,但一個作家如果能做到「敘事基本的精確度」,那麼至少他是上道了。 我的小卡片中有一張是摘自契訶夫(Chekhov)小說裡的句子:「……剎那間他豁然開朗。」我發現這幾個字充滿奇蹟和可能。我愛它的簡單明白,以及它底下暗藏的寓意。還有,神祕感。之前「不清楚」的是什麼?又為什麼現在突然「清楚」了?到底發生了什麼?最要緊的 ── 那現在又如何?在豁然開朗之後會有許多的結果。我感覺有一種徹底的輕鬆 ── 和一種渴望。 我曾無意間聽說作家喬佛瑞.沃爾夫對一群學習寫作的學生說過,寫作「沒有廉價的招式」。這句話應該登上小卡片。不過我想對此做個補充。我討厭招式。在小說裡一個招式或是一個噱頭,不管是廉價的還是經過精心策畫,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在找掩飾。花招最終讓人厭倦,而我是最容易厭倦的人,這可能跟我的注意力無法持久有關。再者,特別花俏、矯揉造作的文筆,或是過分平淡無奇的寫法,也都會引我入睡。寫作人不需要花招或噱頭,甚至不必是團隊中最聰明的傢伙。有時候,一個作家必須能夠心無二用的觀察一些有的沒的,無論是一輪落日或是一隻舊鞋,都能帶着絕對純粹的驚奇 ── 即使讓自己看來像個傻瓜。 約翰.巴思(註:John Simmons Barth,1930-,美國小說家。)幾個月前在《紐約時報書評》上說,十年前他寫作班裡大部分的學生都勇於「形式創新」,這一點現在似乎已經改變了。如今他擔憂的是,寫作人開始在寫一些一九八○年代,老爸老媽式落入俗套的小說。他擔憂這個實驗性就跟自由主義一樣,會過時。如果我發現自己陷入這種陰沉的、所謂「形式改革」的討論,那我就會有些緊張了。因為在我看來,「實驗性」在寫作上往往等同於一張漫不在乎、愚蠢或模仿的證照。甚至更糟,這也等同於一張存心霸凌讀者、疏離讀者的證照。這類寫作多半不會帶給我們任何新的訊息,頂多只是在描述一片貧瘠的風景而已 ──一個人煙罕至、只有這裏那裡出現幾座沙丘和幾隻蜥蜴的地方;一塊人類根本不苟同、無人居住的地方;一塊只有少數科學家感興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真正的實驗性在於原創,極其難能可貴,而且甘味無窮。只要是別人對於事物的看法 ── 比方說,巴塞爾姆的觀點 ── 其他作家就不該依樣畫葫蘆,盲目跟進。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世上只有一個巴塞爾姆,其他人想要以創新之名盜用巴塞爾姆特有的感覺或表現方式,那隻會製造混亂、災難,甚至自欺欺人的後果。真正的實驗性必須是「開創出新的東西」,像龐德(註:即指艾茲拉.龐德。)所倡導的,在創作的過程中自己發現一些新東西。只要寫作的人腦袋還很清楚,而且又不想跟我們脫節,那麼自然會把屬於他們那個世界的消息傳遞給我們。 在一首詩或一個短篇故事裏,作者有可能會描述一些平常的事物 ── 椅子、窗簾、叉子、石頭、女人的耳環之類 ── 以平常卻精準的文字,賦予這些事物一種強大的、甚至令人驚訝的力量。作者也有可能寫一句看來無關痛癢的對話,結果卻能讓讀者背脊發麻 ── 就像納博科夫(註: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國小說家,作品有《蘿莉塔》等。)所做的一樣,而這個,就是藝術快感的源頭。我其實討厭粗鄙、草率的寫法,不管它是不是扛着實驗性的旗號,或只是愚蠢的反映寫實主義。伊薩克.巴別爾(註:Isaac Babel,1894-1940,蘇俄猶太裔小說家。)精採的短篇小說〈莫泊桑〉中,敘事者對於小說的寫法如此說道:「沒有一件利器能比一個位置得當的句號更具殺傷力。」這句話也該登上小卡片。 伊凡.康奈爾(註:Evan Shelby Connell, Jr.,1924-2013,美國詩人,短篇小說作家。)曾提到他何時會知道自己完成了一個短篇:就是在他發現自己看完一遍寫好的短篇,刪掉了其中一些逗點,但是當他再看一遍,又把那些逗點加回原來位置的時候。我喜歡這種工作方式。我尊崇這份認真的態度。畢竟我們擁有的一切就是文字,所以用字最好正確,標點最好點在正確的地方,那才能表達出它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如果用字都是寫作者本身一些毫無節制的私人情緒,或者因為某種理由而不精確(只要文字模糊曖昧都算),就無法抓住讀者的眼睛,也無法滿足讀者的藝術感知,寫出來的東西就變得毫無意義。亨利.詹姆斯(註:Henry James,1843-1916,美國作家。)叫這種無意義的寫作為「差勁的風格」。 有些朋友跟我說他們必須趕着出書,因為缺錢,說是編輯在催稿,或者太太快要離家出走了 ── 諸如此類的理由,所以很抱歉寫得不太好。「要是不這麼趕,我會寫得很好。」我聽到一位寫小說的朋友說這句話的時候,真是無言以對。即使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無言以對。如果我們不能心口如一的寫出內心的想法,那何必寫呢?畢竟,我們能夠帶進墳墓的,不就是我們盡心盡力的過程和辛勤耕耘的結果嗎?我很想對我的朋友說,看在老天的分上,您就轉行吧。換口飯吃,你一定能找到別的比較容易上手,而且看得到實在成果的行業。否則就請你竭盡全力發揮所長,別找理由別找藉口;不要抱怨,不要解釋。 芙蘭納莉.歐康納寫了一篇簡單明瞭、叫做〈寫短篇小說〉的散文,談到寫作是一種發現的行為。歐康納說她經常在坐下來開始寫一個短篇的時候,先要讓自己放空,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往哪去。她說她懷疑很多作家在剛下筆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究竟要往哪兒走(要寫什麼)。她用〈鄉下良民〉為例,說明這個短篇寫到快接近尾聲時,她還沒猜到結局是什麼: 當我開始寫一個故事,我並不知道故事裏有一個裝了一條木腿的博士。我只發現自己某天早上在描述我稍微熟悉的兩個女人,在我還沒弄清楚的時候,我忽然給其中一個女人加了個有一條木腿的女兒。故事繼續發展,我又加進來那個聖經推銷員,但是我毫無概念我該把他怎麼辦。我根本不知道他會去偷那條木腿,一直到寫了一、二十行之後,我發覺事情就該這麼發生的時候,我才清楚這是無可避免的。 幾年前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相當震驚,因為她(或任何人)居然以這種方式在寫小說。我本來以為這是我很難啟口的一個秘密,對此事我一直覺得有些不自在。我相信這種寫作方式等於洩漏了我的缺點。我記得當時看到她的這番話真令我大感振奮。 後來有一次,我坐下來準備寫個短篇(最後成功的把它寫成一個很不錯的故事),沒想到,第一句話就這麼自動跳進來了。其實這句話已經在我腦海裡打轉了好幾天:「電話鈴響的時候,他正在用吸塵器。」我知道故事就在那兒了,就在那兒等人把它說出來。我打從骨子裡感覺得到,這個開頭就是有故事,只要找時間把它寫出來;一旦時間有了,有一整天 ── 十二個,甚至十五個小時 ── 只要我願意好好利用。結果,我做到了,就在這個早上我坐下來寫下第一句,其他的句子便立刻自動自發的彼此吸引出來。我寫短篇就像我寫詩一樣;一行接一行,再接一行。很快的我看見故事在成形,我知道這個就是我的故事,這個正是我想要寫的故事。 我喜歡短篇小說裏面帶有一些威脅感或是惡質的恐嚇。我覺得故事裏帶有一些惡質是好的,至少對故事的轉折是有好處的。我也覺得故事裏必須有緊張感,一種迫在眉睫的東西,一些不安的騷動,否則,就不能成為故事了。想要在小說中創造緊張感,有時是把一些強勁的字眼連在一起,製造出一個有形的畫面;但有時也可能是一些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類似隱喻,隱藏在平順無痕(或支離破碎)的表層底下的景象。 V.S.普里契特(註:Victor Sawdon Pritchett,1900-1997,英國作家,文評家,以短篇小說著稱。)對於短篇小說的定義是「捕捉眼角瞥見的某些東西」。注意這句話裡的「瞥見」。最初只是不經意地一瞥,但之後,這一瞥就擁有了生命,轉變成那瞬間的亮點,如果運氣再好一點 ── 同樣是這個字 ── 更有了後續的結果和意義。短篇小說家的任務,就是窮盡所有力量投入這驚鴻一瞥之中。他會集合他的智慧、文學技巧 (才華)、他的平衡感、他對事物真切的感受,讓讀者知道這些事物究竟是什麼樣子,而他又是如何看待這些事物 ── 就好像別人都不曾看見那樣。要做到這些,勢必要透過清楚精確的語言,用語言把所有細節帶出生命,為讀者點亮這個故事。若要讓細節具體而深入,所使用的語言就必須精準。用字精準的效果看似平淡無奇,卻強大到令人難以料想;只要用對了字,就能切中要害。
到頭來,我們擁有的一切,只有文字。 美國最偉大的 短篇小說家瑞蒙‧卡佛 寫給未來創作者的傳世之書! 33篇從未集結出版之作,繁體中文版首度問世。 專文導讀◎陳榮彬(臺大翻譯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如果作家不能心口如一的寫出內心想法,拜託,快點轉行。」 ──瑞蒙.卡佛 為何卡佛從不寫長篇小說? 誰是將卡佛領進文學窄門的導師? 誰是他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推手? 卡佛心目中的好作品,標準為何? 卡佛給年輕寫作者的建言有哪些? 卡佛出身寒微,十九歲即奉子成婚。接下來的數十年人生裡,他為了一家四口的生計奔忙,屢屢跌入困境,乃至最終亦步上父親後塵,成了酗酒之徒。然而,即便在最困頓時,卡佛對文學的熱愛仍堅持不變,他從二十歲起開始寫作,接下來的二十年,寫作成了他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出口。1983年,他獲得「米德瑞暨哈洛.史特勞斯生活年金獎」,才從經濟窘境中徹底解脫,五年後便因病過世,然而他在短篇小說所奠定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出其右。 -- 一個平凡真誠的「說故事的人」 -陳榮彬(臺大翻譯碩士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任何人的生平若能夠真誠地被述說出來,都可以成一本小說。」 ——引自海明威《死在午後》(Death in the Afternoon) 【為小人物說話】 一九九三年,好萊塢大導演羅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已於二○○六年去世)拍了一部叫做 Short Cuts 的電影,雖然莫名其妙地被台灣片商翻譯成《銀色.性.男女》(可以看到小勞勃.道尼成為「鋼鐵人」之前的青澀模樣!),但從原文不難了解那是一部由許多故事湊起來的電影,而且阿特曼的故事就是取材自當代美國短篇小說名家瑞蒙.卡佛。隔年,時報出版社翻譯出了阿特曼為這電影編的一本卡佛故事集,書名還是叫做 Short Cuts ,中譯本受電影影響,取名為《浮世男女》(已絕版)。把這本故事集中譯本翻開一看,我就手不釋卷了,內心納悶卡佛為什麼可以把那些小人物寫得那麼絕?無論是〈鄰居〉裏面那一對幫鄰居照顧房子的無趣夫妻,或是〈他們不是妳的丈夫〉裏面失業的魯蛇丈夫,還有〈告訴那些娘兒們我們去了〉那兩個一起犯下性暴力重罪的好朋友,都被寫得如此真實。我想,描寫平凡的人生,也是一種本事吧?而且最重要的理由,應該是他自己也經歷過,且看他在本書的〈火〉裏面細數自己做過哪些瑣碎的零工:「在鋸木廠待過,也當過大樓管理員,送貨員,在加油站打工,在庫房打掃……只要說得出的,我都幹過。有一年夏天,在加州的阿克塔 —— 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為了養家活口,白天的時間都在採鬱金香;晚上在餐館打烊之後,我還到一間得來速餐廳做內勤和清理停車場的工作。有一次我甚至考慮應徵收帳員……」。卡佛在這本書裏面,雖然並不是很有系統的,但多少也交代出自己的生平與他短篇小說書寫之關係,值得我們細細體會。 〈談寫作〉 回顧一九六○年代中期,我發現我對於長篇小說有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困擾。有一陣子不管是讀是寫都有困難。我的注意力持續度節節敗退;我完全沒了寫小說的耐心。現在想起來都還是一段冗長而沉悶的經歷。不過我明白,這段過去跟我現在愛寫詩和短篇小說大有關係。直切,直入,不拖泥帶水,毫不遲疑。大概也就在同一時期,在我二十五歲以後的這段時間裏,我失去了強烈的企圖心 ── 若真如此,倒也是好事一樁。企圖心加上一點點的運氣,對於一個有心寫作的人來說是好事。若是企圖心太大加上運氣不好,或者連一點運氣也沒有,那是會要人命的。寫作必須有天分。 有些作家非常有天分;作家應該都有天分吧。但是要擁有看待事物的獨特性和敏銳度,而且能精準貼切的表達出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蓋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當然是作者約翰.厄文(John Irving)心目中最精採的世界。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寫的則是她眼中的世界;另外,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們的世界。契佛(John Cheever)、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以撒.辛格(Isaac Singer)、斯坦利.艾肯(Stanley Elkin)、安.比提(Ann Beattie)、辛西亞.奧茲克(Cynthia Ozick)、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註: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美國後現代主義小說家,重要作品有《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等。得獎無數,被譽為「今日眾多年輕作家的文學教父」。)、瑪莉.羅比森(Mary Robison)、威廉.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貝瑞.漢納(Barry Hannah)、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也各自有他們心中的世界。每一位偉大的或是出色的作家,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造就屬於他的世界。 我上面所說的,其實有些類似「風格」,但風格不是一切。作家在他書寫的每件事物上都簽了字,具有他獨一無二、絕不會錯認的署名。那是他的世界,絕對不會是其他人的。這是造就作家的要件之一,而非天分。有天分的人比比皆是。但一個作家有獨特的見解,而且能夠把見解信達雅的訴諸文字:那麼這個作家就會有一席之地。 伊薩克.狄尼森(註:Baronesse Karen Von Blixen-Finecke,1885-1962,丹麥作家,以英語寫作,伊薩克.狄尼森(Isak Dinesen)為其筆名,其生平曾拍成電影《遠離非洲》。)說她每天都會寫一點東西,沒有指望也沒有絕望。將來我會把這句話記在名片大小的卡片上,貼在我書桌旁的牆壁上。牆壁上現在已經貼了幾張這類3×5的小卡片。其中一張寫着:「敘事基本的精確度是寫作第一也是『唯一』的道德。」是艾茲拉.龐德(註:Ezra 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文學家。)說的。精確「當然」不是一切,但一個作家如果能做到「敘事基本的精確度」,那麼至少他是上道了。 我的小卡片中有一張是摘自契訶夫(Chekhov)小說裡的句子:「……剎那間他豁然開朗。」我發現這幾個字充滿奇蹟和可能。我愛它的簡單明白,以及它底下暗藏的寓意。還有,神祕感。之前「不清楚」的是什麼?又為什麼現在突然「清楚」了?到底發生了什麼?最要緊的 ── 那現在又如何?在豁然開朗之後會有許多的結果。我感覺有一種徹底的輕鬆 ── 和一種渴望。 我曾無意間聽說作家喬佛瑞.沃爾夫對一群學習寫作的學生說過,寫作「沒有廉價的招式」。這句話應該登上小卡片。不過我想對此做個補充。我討厭招式。在小說裡一個招式或是一個噱頭,不管是廉價的還是經過精心策畫,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在找掩飾。花招最終讓人厭倦,而我是最容易厭倦的人,這可能跟我的注意力無法持久有關。再者,特別花俏、矯揉造作的文筆,或是過分平淡無奇的寫法,也都會引我入睡。寫作人不需要花招或噱頭,甚至不必是團隊中最聰明的傢伙。有時候,一個作家必須能夠心無二用的觀察一些有的沒的,無論是一輪落日或是一隻舊鞋,都能帶着絕對純粹的驚奇 ── 即使讓自己看來像個傻瓜。 約翰.巴思(註:John Simmons Barth,1930-,美國小說家。)幾個月前在《紐約時報書評》上說,十年前他寫作班裡大部分的學生都勇於「形式創新」,這一點現在似乎已經改變了。如今他擔憂的是,寫作人開始在寫一些一九八○年代,老爸老媽式落入俗套的小說。他擔憂這個實驗性就跟自由主義一樣,會過時。如果我發現自己陷入這種陰沉的、所謂「形式改革」的討論,那我就會有些緊張了。因為在我看來,「實驗性」在寫作上往往等同於一張漫不在乎、愚蠢或模仿的證照。甚至更糟,這也等同於一張存心霸凌讀者、疏離讀者的證照。這類寫作多半不會帶給我們任何新的訊息,頂多只是在描述一片貧瘠的風景而已 ──一個人煙罕至、只有這裏那裡出現幾座沙丘和幾隻蜥蜴的地方;一塊人類根本不苟同、無人居住的地方;一塊只有少數科學家感興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真正的實驗性在於原創,極其難能可貴,而且甘味無窮。只要是別人對於事物的看法 ── 比方說,巴塞爾姆的觀點 ── 其他作家就不該依樣畫葫蘆,盲目跟進。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世上只有一個巴塞爾姆,其他人想要以創新之名盜用巴塞爾姆特有的感覺或表現方式,那隻會製造混亂、災難,甚至自欺欺人的後果。真正的實驗性必須是「開創出新的東西」,像龐德(註:即指艾茲拉.龐德。)所倡導的,在創作的過程中自己發現一些新東西。只要寫作的人腦袋還很清楚,而且又不想跟我們脫節,那麼自然會把屬於他們那個世界的消息傳遞給我們。 在一首詩或一個短篇故事裏,作者有可能會描述一些平常的事物 ── 椅子、窗簾、叉子、石頭、女人的耳環之類 ── 以平常卻精準的文字,賦予這些事物一種強大的、甚至令人驚訝的力量。作者也有可能寫一句看來無關痛癢的對話,結果卻能讓讀者背脊發麻 ── 就像納博科夫(註: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國小說家,作品有《蘿莉塔》等。)所做的一樣,而這個,就是藝術快感的源頭。我其實討厭粗鄙、草率的寫法,不管它是不是扛着實驗性的旗號,或只是愚蠢的反映寫實主義。伊薩克.巴別爾(註:Isaac Babel,1894-1940,蘇俄猶太裔小說家。)精採的短篇小說〈莫泊桑〉中,敘事者對於小說的寫法如此說道:「沒有一件利器能比一個位置得當的句號更具殺傷力。」這句話也該登上小卡片。 伊凡.康奈爾(註:Evan Shelby Connell, Jr.,1924-2013,美國詩人,短篇小說作家。)曾提到他何時會知道自己完成了一個短篇:就是在他發現自己看完一遍寫好的短篇,刪掉了其中一些逗點,但是當他再看一遍,又把那些逗點加回原來位置的時候。我喜歡這種工作方式。我尊崇這份認真的態度。畢竟我們擁有的一切就是文字,所以用字最好正確,標點最好點在正確的地方,那才能表達出它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如果用字都是寫作者本身一些毫無節制的私人情緒,或者因為某種理由而不精確(只要文字模糊曖昧都算),就無法抓住讀者的眼睛,也無法滿足讀者的藝術感知,寫出來的東西就變得毫無意義。亨利.詹姆斯(註:Henry James,1843-1916,美國作家。)叫這種無意義的寫作為「差勁的風格」。 有些朋友跟我說他們必須趕着出書,因為缺錢,說是編輯在催稿,或者太太快要離家出走了 ── 諸如此類的理由,所以很抱歉寫得不太好。「要是不這麼趕,我會寫得很好。」我聽到一位寫小說的朋友說這句話的時候,真是無言以對。即使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無言以對。如果我們不能心口如一的寫出內心的想法,那何必寫呢?畢竟,我們能夠帶進墳墓的,不就是我們盡心盡力的過程和辛勤耕耘的結果嗎?我很想對我的朋友說,看在老天的分上,您就轉行吧。換口飯吃,你一定能找到別的比較容易上手,而且看得到實在成果的行業。否則就請你竭盡全力發揮所長,別找理由別找藉口;不要抱怨,不要解釋。 芙蘭納莉.歐康納寫了一篇簡單明瞭、叫做〈寫短篇小說〉的散文,談到寫作是一種發現的行為。歐康納說她經常在坐下來開始寫一個短篇的時候,先要讓自己放空,不知道自己究竟該往哪去。她說她懷疑很多作家在剛下筆的時候就知道自己究竟要往哪兒走(要寫什麼)。她用〈鄉下良民〉為例,說明這個短篇寫到快接近尾聲時,她還沒猜到結局是什麼: 當我開始寫一個故事,我並不知道故事裏有一個裝了一條木腿的博士。我只發現自己某天早上在描述我稍微熟悉的兩個女人,在我還沒弄清楚的時候,我忽然給其中一個女人加了個有一條木腿的女兒。故事繼續發展,我又加進來那個聖經推銷員,但是我毫無概念我該把他怎麼辦。我根本不知道他會去偷那條木腿,一直到寫了一、二十行之後,我發覺事情就該這麼發生的時候,我才清楚這是無可避免的。 幾年前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相當震驚,因為她(或任何人)居然以這種方式在寫小說。我本來以為這是我很難啟口的一個秘密,對此事我一直覺得有些不自在。我相信這種寫作方式等於洩漏了我的缺點。我記得當時看到她的這番話真令我大感振奮。 後來有一次,我坐下來準備寫個短篇(最後成功的把它寫成一個很不錯的故事),沒想到,第一句話就這麼自動跳進來了。其實這句話已經在我腦海裡打轉了好幾天:「電話鈴響的時候,他正在用吸塵器。」我知道故事就在那兒了,就在那兒等人把它說出來。我打從骨子裡感覺得到,這個開頭就是有故事,只要找時間把它寫出來;一旦時間有了,有一整天 ── 十二個,甚至十五個小時 ── 只要我願意好好利用。結果,我做到了,就在這個早上我坐下來寫下第一句,其他的句子便立刻自動自發的彼此吸引出來。我寫短篇就像我寫詩一樣;一行接一行,再接一行。很快的我看見故事在成形,我知道這個就是我的故事,這個正是我想要寫的故事。 我喜歡短篇小說裏面帶有一些威脅感或是惡質的恐嚇。我覺得故事裏帶有一些惡質是好的,至少對故事的轉折是有好處的。我也覺得故事裏必須有緊張感,一種迫在眉睫的東西,一些不安的騷動,否則,就不能成為故事了。想要在小說中創造緊張感,有時是把一些強勁的字眼連在一起,製造出一個有形的畫面;但有時也可能是一些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類似隱喻,隱藏在平順無痕(或支離破碎)的表層底下的景象。 V.S.普里契特(註:Victor Sawdon Pritchett,1900-1997,英國作家,文評家,以短篇小說著稱。)對於短篇小說的定義是「捕捉眼角瞥見的某些東西」。注意這句話裡的「瞥見」。最初只是不經意地一瞥,但之後,這一瞥就擁有了生命,轉變成那瞬間的亮點,如果運氣再好一點 ── 同樣是這個字 ── 更有了後續的結果和意義。短篇小說家的任務,就是窮盡所有力量投入這驚鴻一瞥之中。他會集合他的智慧、文學技巧 (才華)、他的平衡感、他對事物真切的感受,讓讀者知道這些事物究竟是什麼樣子,而他又是如何看待這些事物 ── 就好像別人都不曾看見那樣。要做到這些,勢必要透過清楚精確的語言,用語言把所有細節帶出生命,為讀者點亮這個故事。若要讓細節具體而深入,所使用的語言就必須精準。用字精準的效果看似平淡無奇,卻強大到令人難以料想;只要用對了字,就能切中要害。  【本文出處。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本書收錄33篇從未正式發表過的散文隨筆與書評,隱含了卡佛對好作品的準則與期待,不僅讓讀者首次有機會一窺卡佛的生平、經歷,甚至內心世界,更是開啟寫作之路的叩門磚。
【本文出處。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本書收錄33篇從未正式發表過的散文隨筆與書評,隱含了卡佛對好作品的準則與期待,不僅讓讀者首次有機會一窺卡佛的生平、經歷,甚至內心世界,更是開啟寫作之路的叩門磚。[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
|
本篇 |
不想錯過? 請追蹤FB專頁! |
| 喜歡這篇嗎?快分享吧! |
相關文章
快樂生活一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