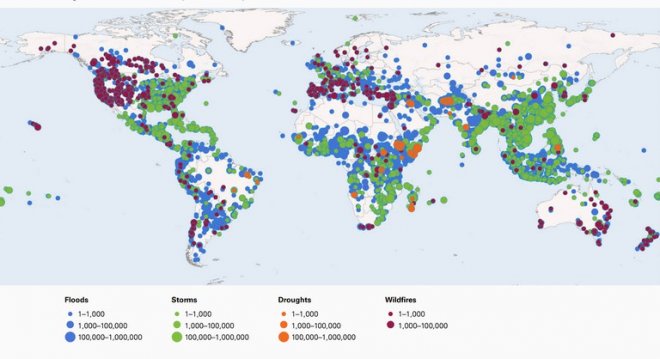「公民不服從」不等於脫序合法化
【聯合報╱社論】 2014.04.19 04:01 am這次學運高掛「公民不服從」的大旗,除發動占領國會、攻占行政院,到後續衍生的群眾包圍警局,乃至反風車團體占領經濟部中庭,均導致警力疲於奔命,而餘波猶未止息。究竟何謂「公民不服從」運動,其界線何在,有必要加以釐清。
「公民不服從」一詞,來自《湖濱散記》作者梭羅在一個半世紀前的一次抗爭。他因不滿美國政府的蓄奴制度及美墨戰爭而拒絕繳稅,從而遭逮捕,在親友代為補繳後隨即獲釋。其後,梭羅寫下了《論公民不服從》一文,說道:「如果一個法律本身很明顯是不正義的,這樣的法律不值得尊重。」其言論,日後深深啟發了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及金恩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
這次學運以「公民不服從」之名來反對服貿協議,並獲年輕世代熱列響應,可見梭羅的感染力不減。但別忘了,梭羅的抗議背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南北戰爭之前,那是另一個時空的事。而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所對抗的英國殖民體制,及非裔美國人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都是國家處於莫大的法制不公之境,因而採取「公民不服從」召喚共同反抗。相形之下,台灣已經民主化二、三十年,學生卻以「公民不服從」來反一件區區服貿協議,不僅是殺雞用牛刀,也曲解了手段。
在這次學生架設的網站上,打出了「我是公民,我不服從」的訴求,號召「人民拆政府」,並宣稱這是「新世代人民的不服從義務」。短短幾句話,卻可看出新世代青年對於「公民不服從」其實缺乏根本的認識。
首先,「公民不服從」運動基本上是在憲政和法治的架構下進行,透過抗議手段表達對特定法律或特定政策的反對,目的並非對政府進行全面式的破壞。而這次學運提出「人民拆政府」的口號,許多人喊得興高采烈,目中毫無政府,也不以民主法治為意。回看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梭羅,他因不服從而抗稅,但他也接受逮捕、繳交罰款;他挑戰的是蓄奴制度,而不是要癱瘓政府。反觀台灣學運,不僅學運領袖標舉支持台獨,它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版本更是架構在「兩國論」的基礎上,還要求以通過監督條例為退場條件。這些表現,皆已逸出公民不服從的原則與範疇。
其次,梭羅認為,當政府淪為暴政或低效而令人無法忍受時,人民有權拒絕向其效忠,並加以抵制。在這裡,梭羅認為「公民不服從」是一項「權利」。然而,在台灣學運的天真宣傳中,卻把不服從說成是一項「義務」。若連權利和義務都分不清,當個「公民」的資格都不夠,能夸夸奢談公民不服從?何況,以馬政府之柔弱,要擔當「暴政」或「獨裁」之名,未免貽笑大方。
第三,「公民不服從」雖以挑戰不正當的法律或政策為目的,但運動者仍應忠於其他國家法制,願意接受法律的懲罰。亦即,行動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法,也願意承受破壞法律的風險。而這次學運的許多參與者,卻以為可以躲在「學運」的光環底下恣意而為,包括入侵行政院、包圍警局、及向分局長說出「暗殺」之語,凡此都已遠遠超越法治的界線。學運一方面侵犯法治,在退場時又要求政府不得「秋後算帳」,否則將重返街頭;這種要脅手法,也有失「公民不服從」的光榮抗爭精神。
我們並不是主張政府應從嚴究辦學運要角,事實上,對於未犯下嚴重脫序行為的參與者,我們認為政府無需過度耗費司法資源窮追猛打。但必須釐清的是:「公民不服從」不是街頭脫序行為合法化的美容膏,社會大眾必須知道其間的界線何在。如果公民不服從可以自命為正當,那麼,服從法治的公民難道都是愚民?
有人批評這次學運有「返祖」現象,原因就在不少參與者對於「公民不服從」這類的民主手段一知半解,且過度濫用,因而助長了理想幼稚化、違法高尚化的問題。這些,由於社會各界對學運的包容,因而不知不覺對民主和法制一再侵蝕。試想,如果有人走進便利超商拿了東西不付錢就走,並聲稱自己是在執行「公民不服從」的抵制財團行動;這種場景,你能想像嗎?如果大家不把界線弄清楚,以當前的氣氛發展下去,那恐怕是遲早的事。

[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
|
本篇 |
不想錯過? 請追蹤FB專頁! |
| 喜歡這篇嗎?快分享吧! |
相關文章
一刻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