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江湖 大佬的背影|封面故事
 sponsored"一場香港黑道人物的葬禮一個階層世代的幾度春秋"14號3月14號,68歲的潘志勇去世後第23天。香港,陰。黃曆上說,這兩日並不適宜行喪。但怎麼說呢,有不得不為之喪事,總有化解之道。潘府治喪,選在這一日守靈。「14號」對過身的潘來說,意義重大。作為香港14K油尖旺區話事人,潘志勇是典型的傳統派黑道人物,好勇鬥狠,講義氣,幫眾擁,權威重。香港社團演變至今,此類人所剩無幾。「14號」曾是這個幫會大本營的門牌號碼,即廣州市寶華路14號。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敗走台灣,一直由國民黨國防情報組資助的洪發山幫眾亦唯有逃離大陸以自保,他們分散抵達香港和澳門後,便以14號作暗號相認。門牌號演化為番號,也成了組織的大寶號。可真實的寶華路14號一度變身麥當勞,如今已改作電器城。sponsored因舊例,黑道人物的白事在世界殯儀館的世界堂進行。靈堂里,三塊液晶屏循環播放著逝者的影像;20個道士吹、拉、彈、擊、唱、噴火、翻跟頭、提燈巡遊、著裝如唐玄奘一樣打坐;上香的人流始於下午3點,幾無間斷,男廁所的擦手紙摞起了一人高;臨街的大門口擺著兩匹帶著號牌的紙紮馬,家人惦記著阿勇賭馬的嗜好;街對面是某旅行社的倉儲外牆,治喪人員在那搭起霸占半壁的竹架,鋪掛滿花牌,也沒見業主家言語;這樣對望的街道兩側,社團幫眾在這頭,O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和反黑組在那頭。就這樣熱鬧了六七個小時。潘志勇在螢幕里,眾人在靈堂里,道士在道場裡,3個世界,一同舞蹈。兩場春茗3月的香港,大家都在忙著春茗。這些俗稱春酒、新年會的聚餐,是各行業各公司各社團開工的號角,也是發財的祝福。又跨過一冬,人們在暖意攀升中笑意盈盈。sponsored我們參加了其中的兩場。一場在銅鑼灣。正在翠苑酒家舉行的是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的spring dinner。英文與粵語在空中飛來飛去,人們穿著晚禮服,排著隊,分開左右兩側,等待乘坐電梯。每位到場者都有名牌,一張夾在胸前,一張對應餐桌的位置。每一張桌都有台號,圍簇著紅酒杯。每一道菜都由侍者分餐到對應人數的小碗里,發給大家。席間有若干次抽獎,直接從禮物箱裡抓取現金紅包,3秒內握住多少,可統統拿走。還有遊戲、唱歌比賽、最佳員工表彰。老闆是個從底層奮鬥上來的人,因為華人慣有的勤懇,得到洋人老闆賞識,把握時機有了今日,在台上慷慨激昂曆數業績,鼓舞人心。伍霆峰帶我們赴了這個優雅的宴會。他是道家白眉派傳人,他的師弟王德,花名疍家,是潘志勇的師父,也是其在14K的大佬。
sponsored"一場香港黑道人物的葬禮一個階層世代的幾度春秋"14號3月14號,68歲的潘志勇去世後第23天。香港,陰。黃曆上說,這兩日並不適宜行喪。但怎麼說呢,有不得不為之喪事,總有化解之道。潘府治喪,選在這一日守靈。「14號」對過身的潘來說,意義重大。作為香港14K油尖旺區話事人,潘志勇是典型的傳統派黑道人物,好勇鬥狠,講義氣,幫眾擁,權威重。香港社團演變至今,此類人所剩無幾。「14號」曾是這個幫會大本營的門牌號碼,即廣州市寶華路14號。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敗走台灣,一直由國民黨國防情報組資助的洪發山幫眾亦唯有逃離大陸以自保,他們分散抵達香港和澳門後,便以14號作暗號相認。門牌號演化為番號,也成了組織的大寶號。可真實的寶華路14號一度變身麥當勞,如今已改作電器城。sponsored因舊例,黑道人物的白事在世界殯儀館的世界堂進行。靈堂里,三塊液晶屏循環播放著逝者的影像;20個道士吹、拉、彈、擊、唱、噴火、翻跟頭、提燈巡遊、著裝如唐玄奘一樣打坐;上香的人流始於下午3點,幾無間斷,男廁所的擦手紙摞起了一人高;臨街的大門口擺著兩匹帶著號牌的紙紮馬,家人惦記著阿勇賭馬的嗜好;街對面是某旅行社的倉儲外牆,治喪人員在那搭起霸占半壁的竹架,鋪掛滿花牌,也沒見業主家言語;這樣對望的街道兩側,社團幫眾在這頭,O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和反黑組在那頭。就這樣熱鬧了六七個小時。潘志勇在螢幕里,眾人在靈堂里,道士在道場裡,3個世界,一同舞蹈。兩場春茗3月的香港,大家都在忙著春茗。這些俗稱春酒、新年會的聚餐,是各行業各公司各社團開工的號角,也是發財的祝福。又跨過一冬,人們在暖意攀升中笑意盈盈。sponsored我們參加了其中的兩場。一場在銅鑼灣。正在翠苑酒家舉行的是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的spring dinner。英文與粵語在空中飛來飛去,人們穿著晚禮服,排著隊,分開左右兩側,等待乘坐電梯。每位到場者都有名牌,一張夾在胸前,一張對應餐桌的位置。每一張桌都有台號,圍簇著紅酒杯。每一道菜都由侍者分餐到對應人數的小碗里,發給大家。席間有若干次抽獎,直接從禮物箱裡抓取現金紅包,3秒內握住多少,可統統拿走。還有遊戲、唱歌比賽、最佳員工表彰。老闆是個從底層奮鬥上來的人,因為華人慣有的勤懇,得到洋人老闆賞識,把握時機有了今日,在台上慷慨激昂曆數業績,鼓舞人心。伍霆峰帶我們赴了這個優雅的宴會。他是道家白眉派傳人,他的師弟王德,花名疍家,是潘志勇的師父,也是其在14K的大佬。 sponsored2016年3月13日,香港元朗,白眉派系第六代傳人伍霆峰先生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伍霆峰自述不是黑道中人,但身在武林。黑道和武林,「沒有重疊」,但「有一個事情是同樣的,就是很多麻煩」。3月14號是伍先生原計劃「封刀」的日子,從此不再收徒,不再過問武林之事。因為潘志勇的喪事,伍霆峰只得把自己的儀式推後。他稱潘志勇「潘先生」,而不是其他人慣用的「勇哥」或者花名「鬍鬚勇」。他說,潘先生「秉性是純的」,「跟他的師父、大哥(王德)的作風一樣,不會去欺負別人,他很守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祖師爺的規矩,不是現代社會的規矩。王德對手下吸毒的小弟,吊著打;「轄區」里食品檔的婆子丟了錢包,也不慌,找王德告狀,准能捉到賊,並看他被大哥教訓。sponsored「在1970到1980那個時間段,在香港,社會不安定,人口很多,這麼小的地方,人跟人之間就有很多摩擦,有錢的人在一堆,有點錢的人在一堆,沒什麼錢的人在一堆,完全沒錢的又一堆,在街上睡的人又一堆,變成一個很畸形、不正常的社會。」伍霆峰說。他在那個年代,坐上飛機,出國留學了。而阿勇中學輟學,跟了大哥,加入了社團,在街上搏命。伍霆峰翻出一張照片,指給我們看,「這位是X哥,他的大佬叫『豆腐佬』,賣豆腐的啦。阿勇他們當年都在九江街上混的。」那日我們乘車,只提到「潘先生」和「花牌」,長發、大隻、肥胖的的士司機便說,「14號,我也會去參加勇哥的『party』。」話畢,竟有點哽咽。我們參加的另一場春茗在詩歌舞街,英文名Sycamore,本意無花果,跟附近街道皆以植物命名的風格匹配,但因嫌無花果不吉利,改作現名。sponsored萬發海鮮菜館的樓梯狹窄,爬到二樓可見指示牌「紅荃小巴」,往來紅磡和荃灣的小巴司機的宴會就在這裡了。到8點時,3桌分布在前中后角落里的麻將蓆已經人聲嘈雜煙霧繚繞。酒席9點開始,那個時間小巴司機才交班。也沒什麼說法,菜端上來大家就動筷子。午夜12點會輪替另一班人馬,再開一次宴。他們穿著帽衫、夾克,戴著粗條的金屬鏈,喝著雪碧可樂和啤酒,直接起身越過桌面取遠端的食物,桌子的轉盤毫無用處。席間他們會談論,14號「給勇哥上香」。幫會組織在香港既敏感,又日常。敏感之處在於,由於法律嚴明、執法嚴格,自稱是三合會組織成員即有入獄風險。而作為一個在本地可以上溯將近二百年歷史的會黨組織,它深入民間,滲透入市民生活的細胞,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中若隱若現但始終存在的一部分,就像在城市脈絡里狂奔的小巴車。sponsored陳慎芝招呼我們吃喝「別客氣」,「這裡都是粗人。」曾為「慈雲山十三太保」之一的陳慎芝,綽號「茅躉華」(「茅躉」指潑皮無賴。「華」取自母名,故其又名陳華,人稱「華哥」),自稱早已退出江湖,他經歷戒毒、信基督,現在已是「洗白了」的商人,幫人戒毒,調節社團間矛盾,曾獲評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一條小巴線,好幾十個家庭……他們沒讀什麼書,考個車牌當司機,每個月也有一兩萬的收入,因為有穩定的工作,所以不會鬧事。你看他們個個都很開心。」陳慎芝講著,不忘說,剛剛跟他們打牌,自己故意輸錢。席間,他向我們介紹一位瘦高的、面部皮膚粗糲的人,他嘴角邊長著一顆大豆般的瘊子,叫「葵佬哥」。西九龍反黑組總督察吳警官指定,葵佬哥為鬍鬚勇葬禮時與警察溝通之人。原因是,葵佬哥「最麻煩了」,「五十多歲了,還很調皮,……下手很狠的。」sponsored吳警官也是厲害角色。日前和勝和坐館上海仔參加手下人葬禮,從車上下來時被吳警官指著罵「你扮紳士啊!」已成為金句。離席時,小弟展開黑西裝外套,幫葵佬哥穿好。幾次會議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見葵佬哥。去年12月,鬍鬚勇曾經帶我們去了葵佬哥看場的歌壇。歌壇像一家老式的茶館,只有個小舞台,「粵雅軒」幾個字由彩燈勾勒,閃爍在大紅背景上。舞台上豎幾把麥克風,掛一道紙牌「歡迎賓客客串,一首小曲壹佰元整」。旁邊牆上貼著歌女的名字和價格,老闆娘在帳簿上記下當天的收益:蕾蕾,600;小蘭,300。賓客們喝著從大瓶里分倒出來的啤酒,把預備點唱的鈔票插在啤酒商贊助的塑料杯里。鬍鬚勇說,這樣的歌廳在廟街又重新流行回來了,增開了很多家,懷戀舊時光的人把這樣的場子填滿、焐熱。
sponsored2016年3月13日,香港元朗,白眉派系第六代傳人伍霆峰先生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伍霆峰自述不是黑道中人,但身在武林。黑道和武林,「沒有重疊」,但「有一個事情是同樣的,就是很多麻煩」。3月14號是伍先生原計劃「封刀」的日子,從此不再收徒,不再過問武林之事。因為潘志勇的喪事,伍霆峰只得把自己的儀式推後。他稱潘志勇「潘先生」,而不是其他人慣用的「勇哥」或者花名「鬍鬚勇」。他說,潘先生「秉性是純的」,「跟他的師父、大哥(王德)的作風一樣,不會去欺負別人,他很守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祖師爺的規矩,不是現代社會的規矩。王德對手下吸毒的小弟,吊著打;「轄區」里食品檔的婆子丟了錢包,也不慌,找王德告狀,准能捉到賊,並看他被大哥教訓。sponsored「在1970到1980那個時間段,在香港,社會不安定,人口很多,這麼小的地方,人跟人之間就有很多摩擦,有錢的人在一堆,有點錢的人在一堆,沒什麼錢的人在一堆,完全沒錢的又一堆,在街上睡的人又一堆,變成一個很畸形、不正常的社會。」伍霆峰說。他在那個年代,坐上飛機,出國留學了。而阿勇中學輟學,跟了大哥,加入了社團,在街上搏命。伍霆峰翻出一張照片,指給我們看,「這位是X哥,他的大佬叫『豆腐佬』,賣豆腐的啦。阿勇他們當年都在九江街上混的。」那日我們乘車,只提到「潘先生」和「花牌」,長發、大隻、肥胖的的士司機便說,「14號,我也會去參加勇哥的『party』。」話畢,竟有點哽咽。我們參加的另一場春茗在詩歌舞街,英文名Sycamore,本意無花果,跟附近街道皆以植物命名的風格匹配,但因嫌無花果不吉利,改作現名。sponsored萬發海鮮菜館的樓梯狹窄,爬到二樓可見指示牌「紅荃小巴」,往來紅磡和荃灣的小巴司機的宴會就在這裡了。到8點時,3桌分布在前中后角落里的麻將蓆已經人聲嘈雜煙霧繚繞。酒席9點開始,那個時間小巴司機才交班。也沒什麼說法,菜端上來大家就動筷子。午夜12點會輪替另一班人馬,再開一次宴。他們穿著帽衫、夾克,戴著粗條的金屬鏈,喝著雪碧可樂和啤酒,直接起身越過桌面取遠端的食物,桌子的轉盤毫無用處。席間他們會談論,14號「給勇哥上香」。幫會組織在香港既敏感,又日常。敏感之處在於,由於法律嚴明、執法嚴格,自稱是三合會組織成員即有入獄風險。而作為一個在本地可以上溯將近二百年歷史的會黨組織,它深入民間,滲透入市民生活的細胞,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中若隱若現但始終存在的一部分,就像在城市脈絡里狂奔的小巴車。sponsored陳慎芝招呼我們吃喝「別客氣」,「這裡都是粗人。」曾為「慈雲山十三太保」之一的陳慎芝,綽號「茅躉華」(「茅躉」指潑皮無賴。「華」取自母名,故其又名陳華,人稱「華哥」),自稱早已退出江湖,他經歷戒毒、信基督,現在已是「洗白了」的商人,幫人戒毒,調節社團間矛盾,曾獲評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一條小巴線,好幾十個家庭……他們沒讀什麼書,考個車牌當司機,每個月也有一兩萬的收入,因為有穩定的工作,所以不會鬧事。你看他們個個都很開心。」陳慎芝講著,不忘說,剛剛跟他們打牌,自己故意輸錢。席間,他向我們介紹一位瘦高的、面部皮膚粗糲的人,他嘴角邊長著一顆大豆般的瘊子,叫「葵佬哥」。西九龍反黑組總督察吳警官指定,葵佬哥為鬍鬚勇葬禮時與警察溝通之人。原因是,葵佬哥「最麻煩了」,「五十多歲了,還很調皮,……下手很狠的。」sponsored吳警官也是厲害角色。日前和勝和坐館上海仔參加手下人葬禮,從車上下來時被吳警官指著罵「你扮紳士啊!」已成為金句。離席時,小弟展開黑西裝外套,幫葵佬哥穿好。幾次會議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見葵佬哥。去年12月,鬍鬚勇曾經帶我們去了葵佬哥看場的歌壇。歌壇像一家老式的茶館,只有個小舞台,「粵雅軒」幾個字由彩燈勾勒,閃爍在大紅背景上。舞台上豎幾把麥克風,掛一道紙牌「歡迎賓客客串,一首小曲壹佰元整」。旁邊牆上貼著歌女的名字和價格,老闆娘在帳簿上記下當天的收益:蕾蕾,600;小蘭,300。賓客們喝著從大瓶里分倒出來的啤酒,把預備點唱的鈔票插在啤酒商贊助的塑料杯里。鬍鬚勇說,這樣的歌廳在廟街又重新流行回來了,增開了很多家,懷戀舊時光的人把這樣的場子填滿、焐熱。 2015年12月18日,香港廟街,鬍鬚勇和弟弟潘志泉(綽號十叔,右二)到葵佬(左二)的粵雅軒歌廳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葵佬哥向店裡的女主管介紹鬍鬚勇。這個上了些歲數的女人臉上寫滿恭敬:「勇哥(的名字)我聽了很久了,不過沒見過。」「開張都叫不了他來,今天來了,謝謝勇哥!」葵佬哥說。他更喜歡在自己做股東的現代化夜總會裡唱歌,而且多是英文歌。如果誰沒有眼色剛好擋住了他看螢幕上的歌詞,他會極不耐煩地揮手令其躲開。這天在老式歌廳,在小弟們的歡呼聲中,鬍鬚勇唱了三首歌,《榕樹下》、《往事只能回味》和一首不斷重複I did love you的英文歌。坐在舞台附近的一位老人家,伴著歌聲,打起了瞌睡。鬍鬚勇也懷戀舊時光。三四十歲正值當打之年,麻雀館、夜總會都請他去看場,「紅」得「差不多天天有新聞」。警察要破案,有時不得不對黑社會有所倚仗,貪污尋租也有,黑白兩道中人可以在夜店勾肩搭背稱兄道弟。不像現在,必須涇渭分明,完全沒有朋友做。那個時代,商人也要依靠黑社會,求財討債保安寧。他還懷念那個時候「人淳樸一點,你肯幹活,兩餐不憂,沒那麼多壓迫感」,而現在的社會「像個壓力煲」。換作如今這個年代,他可能都不會加入黑社會了。「我經常叫人不要入黑社會,加入黑社會還慘過去做正行。」眾人起身敬酒,鬍鬚勇拿掉杯蓋,舉起冒著熱氣的茶水。他患癌症十年,酒已經不能喝。頭髮也剃光,他出門戴鴨舌帽,每天換,不重樣。與病魔鬥爭的經年累月,已經被醫生們稱作「神跡」。同時期的病友都死了,他還會在覺得精神好的時候出門打麻將,每周三的賭馬也從不落下。伍霆峰覺得,大概街上殺伐的經驗,讓鬍鬚勇習慣了與痛相處。「打打殺殺不辛苦,癌症挺辛苦。打打殺殺一次過,贏就贏,輸就輸,(之後還)可以再來過。癌症你很難勝過它,你受到攻擊,就避它,不可以跟它拼搏。只有你傷,它不傷。這跟江湖不同。」鬍鬚勇一直不服、不甘,堅持挺過了猴年春節,去世於正月十三。在守靈日,葵佬哥等一眾兩百餘人,黑西裝、黑襯衫、黑領帶、黑皮鞋,胸前戴著「知賓」黑白符。他們是鬍鬚勇門下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弟」,分成幾隊,擺布花牌、在靈堂黃毯兩側站位、與警察接觸、接待賓客,還負責安保、舞獅、後勤等,每隊一個頭目,配對講機、藍牙耳機,換班制執行。為此,葬禮前曾專門「開了幾次會」安排部署。就拿擺花牌來說,上千個花牌,送禮之人的重要性和與逝者的親密度不同,擺放的位置也不同。比如「勝利堂上海哥」送的花牌,剛剛還在走廊洗手間門口看到,過一會兒便不知所蹤。「摯友尹國駒」送的,本來擺在靈堂正中顯著位置,未幾便不見,原因是「香港不給『崩牙駒』入境」。鬍鬚勇的弟弟潘志泉驕傲於這麼大規模儀式的「紀律性、整齊度」,「不會叉腰蹺腳文武腳,而且很少在靈堂里高聲講話、談笑。他們是很認真的。他們很尊重勇哥。他們是很自發的,不是生硬去做,不用監管,做什麼都好。(分工明確,很整齊,)很感動,這是很開心的一樣事情。」潘志泉小鬍鬚勇8歲,排行老十,人稱「阿十」、「十叔」。鬍鬚勇最後這段日子每次採訪時,都會叫他陪伴左右。阿十估計14號上香的人有兩三千。陳建國在一旁補充,「我聽有些警察說是有四千五百多,但是後來又有些是說三千多。」52歲的陳建國是原香港西九龍警署反黑組探員,2005年因被指控自稱黑社會成員而入獄。他外表高大有型,但說起話來總是充滿猶豫。鬍鬚勇說陳建國甫一出獄時,境況糟糕,自己曾出手相助。「其實沒什麼需要他直接幫我,可能其他社團、其他人知道我跟了勇哥後,已經是一個方便了,或者說是他給了我的財富來源之一。……(比方說)如果我在不跟勇哥的情況下,在缽蘭街開一家酒吧,別人會來收保護費啊,叫你給場他看,而如果別人知道你跟了勇哥的,就不會有人來談這個了,……我們在外面講數(談判)期間,因為大家認識的,你是勇哥的人,那就OK啦,就這麼算了吧,會將事情很低調地處理,外面的很多老闆給面子。」「我自己覺得,警察有壞有好,警察裡面也有壞分子,黑社會裡也有很正經的人,你說要我怎麼界定……當時我上班的時候,百分之百是個警察,但是我收了工,我可能是以一個警察身份出去結交朋友,可因為我在紀律部隊,當然受到很多限制……但其實,黑社會真的全是壞人嗎,警察是全是好人嗎?……其實黑社會不一定會做犯法的事,比如我發現我被別人欺負,報警沒有人來查,就只好找當地(黑幫),雖然警察跟黑社會是沒有(灰色地帶),是黑就黑,是白就白……」陳建國說,這次葬禮,驚動警隊諸多部門,跨地區跨部門,有O記,也有西九龍、新界等地的反黑組,「我想,人數都過百人了。」「那(賓客數量)就是三四千多,警察很少報大數的。」阿十說,因為「報多了那就等於幫他(勇哥)壯大了聲勢,不可能這樣。」香港媒體稱,本次葬禮的規模「近年罕見」。各社團坐館或前坐館、堂口大佬基本都到場祭拜。準備會議上,眾人最怕來賓在進場過程中與警察有衝突。在現場,葵佬哥就常從手下那裡得知,「O記在查XX(來賓)的證件。」為了控制衝突,「在他進來的時候,我們會讓人去跟警察說,有分量的人你就給他進來吧,年輕的就查一下身份證咯。如果有什麼起鬨,我們就讓負責這方面的兄弟去說,『忍一下,尊重一下勇哥,不要跟警察發生摩擦』。」但是按照江湖規矩,預防針不能提前打,「不能給別人開條件。」在香燭煙氣瀰漫的場子裡,空氣正是靠著這上千人次的走位動作而帶著流動。在人口密度最大時,人群逆向成排,擠擠挨挨地蛇形扭動。八人扶靈世界殯儀館的布告欄是玻璃質地,映著燈光、人影和花形。棕黃色的油漆在上面打著表格,白漆書寫姓名和時辰——潘志勇,十五日,十二時,出殯。為鬍鬚勇扶靈的有8位先生。據阿十說,選擇標準是「交情」和「江湖地位」。扶靈人之一的陳慎芝,此前一天帶我們去了佐敦西貢街的適香園茶餐廳,對面的婚宴酒樓,在上世紀90年代末曾是全香港最熱的迪斯科場子348,聞名東南亞。每天晚上9點人們在門口排隊等待入場,轟轟隆隆到早上9點。迪斯科包下樓上大華酒店10間房,還是沒法做到隔震。凌晨1點到4點,是酒過幾巡後打架頻發的時段。鬍鬚勇是348的股東之一。
2015年12月18日,香港廟街,鬍鬚勇和弟弟潘志泉(綽號十叔,右二)到葵佬(左二)的粵雅軒歌廳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葵佬哥向店裡的女主管介紹鬍鬚勇。這個上了些歲數的女人臉上寫滿恭敬:「勇哥(的名字)我聽了很久了,不過沒見過。」「開張都叫不了他來,今天來了,謝謝勇哥!」葵佬哥說。他更喜歡在自己做股東的現代化夜總會裡唱歌,而且多是英文歌。如果誰沒有眼色剛好擋住了他看螢幕上的歌詞,他會極不耐煩地揮手令其躲開。這天在老式歌廳,在小弟們的歡呼聲中,鬍鬚勇唱了三首歌,《榕樹下》、《往事只能回味》和一首不斷重複I did love you的英文歌。坐在舞台附近的一位老人家,伴著歌聲,打起了瞌睡。鬍鬚勇也懷戀舊時光。三四十歲正值當打之年,麻雀館、夜總會都請他去看場,「紅」得「差不多天天有新聞」。警察要破案,有時不得不對黑社會有所倚仗,貪污尋租也有,黑白兩道中人可以在夜店勾肩搭背稱兄道弟。不像現在,必須涇渭分明,完全沒有朋友做。那個時代,商人也要依靠黑社會,求財討債保安寧。他還懷念那個時候「人淳樸一點,你肯幹活,兩餐不憂,沒那麼多壓迫感」,而現在的社會「像個壓力煲」。換作如今這個年代,他可能都不會加入黑社會了。「我經常叫人不要入黑社會,加入黑社會還慘過去做正行。」眾人起身敬酒,鬍鬚勇拿掉杯蓋,舉起冒著熱氣的茶水。他患癌症十年,酒已經不能喝。頭髮也剃光,他出門戴鴨舌帽,每天換,不重樣。與病魔鬥爭的經年累月,已經被醫生們稱作「神跡」。同時期的病友都死了,他還會在覺得精神好的時候出門打麻將,每周三的賭馬也從不落下。伍霆峰覺得,大概街上殺伐的經驗,讓鬍鬚勇習慣了與痛相處。「打打殺殺不辛苦,癌症挺辛苦。打打殺殺一次過,贏就贏,輸就輸,(之後還)可以再來過。癌症你很難勝過它,你受到攻擊,就避它,不可以跟它拼搏。只有你傷,它不傷。這跟江湖不同。」鬍鬚勇一直不服、不甘,堅持挺過了猴年春節,去世於正月十三。在守靈日,葵佬哥等一眾兩百餘人,黑西裝、黑襯衫、黑領帶、黑皮鞋,胸前戴著「知賓」黑白符。他們是鬍鬚勇門下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弟」,分成幾隊,擺布花牌、在靈堂黃毯兩側站位、與警察接觸、接待賓客,還負責安保、舞獅、後勤等,每隊一個頭目,配對講機、藍牙耳機,換班制執行。為此,葬禮前曾專門「開了幾次會」安排部署。就拿擺花牌來說,上千個花牌,送禮之人的重要性和與逝者的親密度不同,擺放的位置也不同。比如「勝利堂上海哥」送的花牌,剛剛還在走廊洗手間門口看到,過一會兒便不知所蹤。「摯友尹國駒」送的,本來擺在靈堂正中顯著位置,未幾便不見,原因是「香港不給『崩牙駒』入境」。鬍鬚勇的弟弟潘志泉驕傲於這麼大規模儀式的「紀律性、整齊度」,「不會叉腰蹺腳文武腳,而且很少在靈堂里高聲講話、談笑。他們是很認真的。他們很尊重勇哥。他們是很自發的,不是生硬去做,不用監管,做什麼都好。(分工明確,很整齊,)很感動,這是很開心的一樣事情。」潘志泉小鬍鬚勇8歲,排行老十,人稱「阿十」、「十叔」。鬍鬚勇最後這段日子每次採訪時,都會叫他陪伴左右。阿十估計14號上香的人有兩三千。陳建國在一旁補充,「我聽有些警察說是有四千五百多,但是後來又有些是說三千多。」52歲的陳建國是原香港西九龍警署反黑組探員,2005年因被指控自稱黑社會成員而入獄。他外表高大有型,但說起話來總是充滿猶豫。鬍鬚勇說陳建國甫一出獄時,境況糟糕,自己曾出手相助。「其實沒什麼需要他直接幫我,可能其他社團、其他人知道我跟了勇哥後,已經是一個方便了,或者說是他給了我的財富來源之一。……(比方說)如果我在不跟勇哥的情況下,在缽蘭街開一家酒吧,別人會來收保護費啊,叫你給場他看,而如果別人知道你跟了勇哥的,就不會有人來談這個了,……我們在外面講數(談判)期間,因為大家認識的,你是勇哥的人,那就OK啦,就這麼算了吧,會將事情很低調地處理,外面的很多老闆給面子。」「我自己覺得,警察有壞有好,警察裡面也有壞分子,黑社會裡也有很正經的人,你說要我怎麼界定……當時我上班的時候,百分之百是個警察,但是我收了工,我可能是以一個警察身份出去結交朋友,可因為我在紀律部隊,當然受到很多限制……但其實,黑社會真的全是壞人嗎,警察是全是好人嗎?……其實黑社會不一定會做犯法的事,比如我發現我被別人欺負,報警沒有人來查,就只好找當地(黑幫),雖然警察跟黑社會是沒有(灰色地帶),是黑就黑,是白就白……」陳建國說,這次葬禮,驚動警隊諸多部門,跨地區跨部門,有O記,也有西九龍、新界等地的反黑組,「我想,人數都過百人了。」「那(賓客數量)就是三四千多,警察很少報大數的。」阿十說,因為「報多了那就等於幫他(勇哥)壯大了聲勢,不可能這樣。」香港媒體稱,本次葬禮的規模「近年罕見」。各社團坐館或前坐館、堂口大佬基本都到場祭拜。準備會議上,眾人最怕來賓在進場過程中與警察有衝突。在現場,葵佬哥就常從手下那裡得知,「O記在查XX(來賓)的證件。」為了控制衝突,「在他進來的時候,我們會讓人去跟警察說,有分量的人你就給他進來吧,年輕的就查一下身份證咯。如果有什麼起鬨,我們就讓負責這方面的兄弟去說,『忍一下,尊重一下勇哥,不要跟警察發生摩擦』。」但是按照江湖規矩,預防針不能提前打,「不能給別人開條件。」在香燭煙氣瀰漫的場子裡,空氣正是靠著這上千人次的走位動作而帶著流動。在人口密度最大時,人群逆向成排,擠擠挨挨地蛇形扭動。八人扶靈世界殯儀館的布告欄是玻璃質地,映著燈光、人影和花形。棕黃色的油漆在上面打著表格,白漆書寫姓名和時辰——潘志勇,十五日,十二時,出殯。為鬍鬚勇扶靈的有8位先生。據阿十說,選擇標準是「交情」和「江湖地位」。扶靈人之一的陳慎芝,此前一天帶我們去了佐敦西貢街的適香園茶餐廳,對面的婚宴酒樓,在上世紀90年代末曾是全香港最熱的迪斯科場子348,聞名東南亞。每天晚上9點人們在門口排隊等待入場,轟轟隆隆到早上9點。迪斯科包下樓上大華酒店10間房,還是沒法做到隔震。凌晨1點到4點,是酒過幾巡後打架頻發的時段。鬍鬚勇是348的股東之一。 香港慈雲山,右為陳慎芝 圖 /本刊記者方迎忠陳慎芝也去過這個夜場,描述裡面「烏煙瘴氣」,「喝醉酒就這樣(好打架)的了。我們有句話說,喝醉酒大哥變鷯哥(八哥),鷯哥變大哥,明明自己郵差(郵遞員)又說自己是雜差(便衣警察),喝高了亂說話!」場子熱鬧,帶火了一整條街的商鋪。因為暴力事件頻發,當局要求關閉348。商鋪的經營者聯名要求重開,但住戶們不同意。陳慎芝當時作為顧問,幫忙想辦法,讓迪斯科聘用九十多個釋囚,於是跟法庭申請,希望給這些人改過自新重回社會的機會。法庭批准試用3個月,還是爭鬧不斷,最終勒令關停了鋪面。當年的鬍鬚勇,在夜裡唱完歌后,便來適香園喝咖啡。陳慎芝念叨著「懷念勇哥」,在店門口撞到老闆郭生。郭生說,知了,「在報紙上看到。」「這家餐廳很多故事。」陳慎芝說。適香園是很多聊天、講數、拆彈(談和)、毒品交易發生的場所。它是這條街上第一家餐館,39年來保持著不變的十幾張台的格局和綠橙色搭配的桌椅,咖啡從5毛漲到15塊,熱鬧的時段從當初的半夜改成了如今的下午。「郭生,這家餐廳開了多少年?」落了座的陳慎芝問。頭戴毛線帽子的郭生緩緩地轉過頭,「39年。」「八十幾歲了啊郭生?」「83歲。」鬍鬚勇說茅躉華,「不是很好鬥的人,就是(曾經)吸毒。但是他的人緣不錯,對人很好。」鬍鬚勇病中,陳慎芝曾打電話給他,「我說不出話來,他就講笑逗我,他叫我潘先生,我叫他陳先生,他就講啊講啊,見我說不出話來,突然哭起來。他說,潘先生啊,我很捨不得你啊。」兩個月前,茅躉華在電話里對鬍鬚勇說,「你要堅持住啊,來看我首映。」陳慎芝的自傳電影預計今年上映,主演是劉青雲。鬍鬚勇回他:「我感覺到自己沒有力氣再支持了。」茅躉華說鬍鬚勇「是惡人,但是講理的惡人」,「是梟雄。」「梟雄啊,(就是)會有些不正確的手段(去坐到這個位置),當然,如果你問我如今這個世界上能有多少個人去用正確的手段去做到一件事,我想很難回答……他打了幾場大架打出名了。他很多朋友愛戴,(因為)如果朋友有什麼事情,他一定會站出來,不會逃避的,這個是最重要的。」
香港慈雲山,右為陳慎芝 圖 /本刊記者方迎忠陳慎芝也去過這個夜場,描述裡面「烏煙瘴氣」,「喝醉酒就這樣(好打架)的了。我們有句話說,喝醉酒大哥變鷯哥(八哥),鷯哥變大哥,明明自己郵差(郵遞員)又說自己是雜差(便衣警察),喝高了亂說話!」場子熱鬧,帶火了一整條街的商鋪。因為暴力事件頻發,當局要求關閉348。商鋪的經營者聯名要求重開,但住戶們不同意。陳慎芝當時作為顧問,幫忙想辦法,讓迪斯科聘用九十多個釋囚,於是跟法庭申請,希望給這些人改過自新重回社會的機會。法庭批准試用3個月,還是爭鬧不斷,最終勒令關停了鋪面。當年的鬍鬚勇,在夜裡唱完歌后,便來適香園喝咖啡。陳慎芝念叨著「懷念勇哥」,在店門口撞到老闆郭生。郭生說,知了,「在報紙上看到。」「這家餐廳很多故事。」陳慎芝說。適香園是很多聊天、講數、拆彈(談和)、毒品交易發生的場所。它是這條街上第一家餐館,39年來保持著不變的十幾張台的格局和綠橙色搭配的桌椅,咖啡從5毛漲到15塊,熱鬧的時段從當初的半夜改成了如今的下午。「郭生,這家餐廳開了多少年?」落了座的陳慎芝問。頭戴毛線帽子的郭生緩緩地轉過頭,「39年。」「八十幾歲了啊郭生?」「83歲。」鬍鬚勇說茅躉華,「不是很好鬥的人,就是(曾經)吸毒。但是他的人緣不錯,對人很好。」鬍鬚勇病中,陳慎芝曾打電話給他,「我說不出話來,他就講笑逗我,他叫我潘先生,我叫他陳先生,他就講啊講啊,見我說不出話來,突然哭起來。他說,潘先生啊,我很捨不得你啊。」兩個月前,茅躉華在電話里對鬍鬚勇說,「你要堅持住啊,來看我首映。」陳慎芝的自傳電影預計今年上映,主演是劉青雲。鬍鬚勇回他:「我感覺到自己沒有力氣再支持了。」茅躉華說鬍鬚勇「是惡人,但是講理的惡人」,「是梟雄。」「梟雄啊,(就是)會有些不正確的手段(去坐到這個位置),當然,如果你問我如今這個世界上能有多少個人去用正確的手段去做到一件事,我想很難回答……他打了幾場大架打出名了。他很多朋友愛戴,(因為)如果朋友有什麼事情,他一定會站出來,不會逃避的,這個是最重要的。」 鬍鬚勇(中)的婚禮鬍鬚勇不相信黑道中人能夠真正洗白,即便陳慎芝也一樣,「很難形容的。你說他不是(黑道中人)吧,看起來又是。你說是吧,看起來又不是。他是中間人。他兩方面(都在)。他沒有脫離的。」至於「脫離」,「其實沒有什麼可以界定的。比如,你說我退出三合會了,但很少有人這樣子……因為有人會笑你。」陳慎芝在江湖上得到過「拆彈專家」的稱號。「如果他說他跟我們的兄弟沒有關係,他很多地方不行的。拆什麼彈啊,沒有能力沒有背景拆什麼拆,人家不給你面子。所以你不可以脫離,脫離了沒有關係,你就沒有力量。」鬍鬚勇說。陳慎芝說勇哥也是拆彈專家,「我看到有一次吵架,他走過去(大聲)說,吵什麼!他們就不吵了。我就不是,我會(和事佬一樣)說不要吵啦。他是權威性,我是友誼性。」鬍鬚勇知道陳慎芝手下已沒有小弟,會不時詢問他是否需要幫忙。「我曾經說,我沒事的,如果我有什麼事我就報警。他說,報警?有沒有搞錯,你大哥來的啊,給人笑!我說,大哥不可以報警嗎?」在2014年生日宴上,陳慎芝說,「我們每一個人出生都拿著一副爛牌,但今天我們能把牌打成好牌,是不簡單的。」扶靈的人中,還有陳秉寰、馬文川(「馬細」),二人連同鬍鬚勇、司徒玉蓮、「街市偉」都出自深水埗九江街,從小一起長大。深水埗在當時是有名的貧民窟。後來這幾人都成了叱吒風雲的人物。他們當年活動的九江街,曾被稱為「惡人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幫會成員不稱呼自己為14號,而是說「來自九江街」。司徒玉蓮發簾有一綹白,氣場足。她的事業在澳門,丈夫「街市偉」也是江湖猛人。鬍鬚勇形容司徒玉蓮「是一個女強人」,「她想得很大,她做的事很大,小的事情不做,同時她看得很準的,腦筋很靈光。她有她的克制力。她到賭場跟武則天差不多,員工看到她就立正。普通的女人在賭場怎麼可以做到這樣,那是一個男性(稱)大的地方,但是她可以。」「都是得到勇哥他們江湖人(的支持),我跟江湖人是離不開關係的,他們大部分支持我的。你也知道在澳門這個無返之地,如果沒有勇哥這些江湖朋友,不要說女的,男的也難待。」司徒玉蓮描述鬍鬚勇對她的幫助,「是無形的幫」,很簡單,「江湖裡他說一句,這個人不錯,就幫了很大的忙。」而反過來,在澳門,若鬍鬚勇的小弟惹事,司徒玉蓮也就幫著紓困。今年1月,在吳淞路的旦哥火鍋店,司徒玉蓮同電影人李修賢一起,陪鬍鬚勇接受採訪。火鍋店是他們幾個朋友合開的。這是鬍鬚勇最後一次受訪。鬍鬚勇打趣司徒玉蓮管著賭場卻賭技太差。司徒玉蓮對鬍鬚勇回憶當年追求他的女孩佯裝嘲諷,然後幫他打開熱檸茶,加糖,嘗一下甜度,滿意了,推到這個停不下回憶的男人面前。
鬍鬚勇(中)的婚禮鬍鬚勇不相信黑道中人能夠真正洗白,即便陳慎芝也一樣,「很難形容的。你說他不是(黑道中人)吧,看起來又是。你說是吧,看起來又不是。他是中間人。他兩方面(都在)。他沒有脫離的。」至於「脫離」,「其實沒有什麼可以界定的。比如,你說我退出三合會了,但很少有人這樣子……因為有人會笑你。」陳慎芝在江湖上得到過「拆彈專家」的稱號。「如果他說他跟我們的兄弟沒有關係,他很多地方不行的。拆什麼彈啊,沒有能力沒有背景拆什麼拆,人家不給你面子。所以你不可以脫離,脫離了沒有關係,你就沒有力量。」鬍鬚勇說。陳慎芝說勇哥也是拆彈專家,「我看到有一次吵架,他走過去(大聲)說,吵什麼!他們就不吵了。我就不是,我會(和事佬一樣)說不要吵啦。他是權威性,我是友誼性。」鬍鬚勇知道陳慎芝手下已沒有小弟,會不時詢問他是否需要幫忙。「我曾經說,我沒事的,如果我有什麼事我就報警。他說,報警?有沒有搞錯,你大哥來的啊,給人笑!我說,大哥不可以報警嗎?」在2014年生日宴上,陳慎芝說,「我們每一個人出生都拿著一副爛牌,但今天我們能把牌打成好牌,是不簡單的。」扶靈的人中,還有陳秉寰、馬文川(「馬細」),二人連同鬍鬚勇、司徒玉蓮、「街市偉」都出自深水埗九江街,從小一起長大。深水埗在當時是有名的貧民窟。後來這幾人都成了叱吒風雲的人物。他們當年活動的九江街,曾被稱為「惡人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幫會成員不稱呼自己為14號,而是說「來自九江街」。司徒玉蓮發簾有一綹白,氣場足。她的事業在澳門,丈夫「街市偉」也是江湖猛人。鬍鬚勇形容司徒玉蓮「是一個女強人」,「她想得很大,她做的事很大,小的事情不做,同時她看得很準的,腦筋很靈光。她有她的克制力。她到賭場跟武則天差不多,員工看到她就立正。普通的女人在賭場怎麼可以做到這樣,那是一個男性(稱)大的地方,但是她可以。」「都是得到勇哥他們江湖人(的支持),我跟江湖人是離不開關係的,他們大部分支持我的。你也知道在澳門這個無返之地,如果沒有勇哥這些江湖朋友,不要說女的,男的也難待。」司徒玉蓮描述鬍鬚勇對她的幫助,「是無形的幫」,很簡單,「江湖裡他說一句,這個人不錯,就幫了很大的忙。」而反過來,在澳門,若鬍鬚勇的小弟惹事,司徒玉蓮也就幫著紓困。今年1月,在吳淞路的旦哥火鍋店,司徒玉蓮同電影人李修賢一起,陪鬍鬚勇接受採訪。火鍋店是他們幾個朋友合開的。這是鬍鬚勇最後一次受訪。鬍鬚勇打趣司徒玉蓮管著賭場卻賭技太差。司徒玉蓮對鬍鬚勇回憶當年追求他的女孩佯裝嘲諷,然後幫他打開熱檸茶,加糖,嘗一下甜度,滿意了,推到這個停不下回憶的男人面前。 2016年1月19日,香港尖沙咀,鬍鬚勇和澳門大姐大司徒玉蓮回憶當年在深水埗九江街的日子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鬍鬚勇說,回憶的總是那些「鑽石」一樣的東西,過去和現在並無分別,「不過現在你想,可能你覺得這個江湖你(將要)離去了,有些感觸。」他指著上次採訪時他穿花襯衫的照片,說,「照片里就是那個小弟被人砍的地方。那個火鍋店的後門。小弟有幾個被槍打死,被刀砍死。幾個了,斌仔(音譯)無期徒刑,阿藥(音譯)失蹤,球仔(音譯)在台灣被槍打死,死了兩天都不知,像電影一樣,現在想想比電影還真實。」身體還好時,他會在大風的日子裡撐著傘到他們死去的地方憑弔。最後一次憑弔都已經是7年前的事情。「這7年不斷有些新的病死了老死了,我就想,都不知能憑弔多少,還不如躺在床上思念。」他講起一篇寫了一半的回憶文章,裡面有廟街的妓女,很多小賭檔。那裡有很多大榕樹。還有座大廟,香火很旺。「解簽,求姻緣,專騙你們這些孝女。(廟中人)用麻雀挑簽,麻雀都是經過訓練的,其實每個簽放了不同味道的米,讓麻雀跳著去選,稱『這是麻雀挑的,不是我挑的』,說是『天意』。」現在,大榕樹都砍掉,大廟變成花園。「廟街以前吃的也便宜,衣服也便宜,什麼都便宜。潮汕人做的貝殼類食物也都很好。都在那裡。現在想起來都很過癮。現在去廟街已經看不到以前香港的東西了。香港以前的天星碼頭,現在也沒有了。」「以前的小電影,色情電影,普通人看不到,要給錢,到接駁口,是個巴士。你想看黃片,就在那裡等。坐夠一車人就拉到觀塘。那個站是14K控制的。」「第一次砍人,跳上車,腦袋一片空白,太緊張。」「當時打過好多地方,控制好多地方,自己到現在都不記得了。別人說你曾經……我說我不記得了……」他說,那篇文章還想寫,「有一個幫會,在那個區域很厲害,不准其他幫會在那裡開賭檔。我曾經帶我的小弟去那裡掃掉了他們的檔口。四十多年前,我二十多歲。」三隻孝獅除了家人,司徒玉蓮在靈前哭得最多。一哭,她就立刻掏出墨鏡戴上。「要舞獅了。」有小弟特意跑來通知我們出去看。3隻黑白藍素色的獅子緩步向前,眼睛半張,鼓點和鑼聲低且輕,舞獅人跪著挪入靈堂。
2016年1月19日,香港尖沙咀,鬍鬚勇和澳門大姐大司徒玉蓮回憶當年在深水埗九江街的日子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鬍鬚勇說,回憶的總是那些「鑽石」一樣的東西,過去和現在並無分別,「不過現在你想,可能你覺得這個江湖你(將要)離去了,有些感觸。」他指著上次採訪時他穿花襯衫的照片,說,「照片里就是那個小弟被人砍的地方。那個火鍋店的後門。小弟有幾個被槍打死,被刀砍死。幾個了,斌仔(音譯)無期徒刑,阿藥(音譯)失蹤,球仔(音譯)在台灣被槍打死,死了兩天都不知,像電影一樣,現在想想比電影還真實。」身體還好時,他會在大風的日子裡撐著傘到他們死去的地方憑弔。最後一次憑弔都已經是7年前的事情。「這7年不斷有些新的病死了老死了,我就想,都不知能憑弔多少,還不如躺在床上思念。」他講起一篇寫了一半的回憶文章,裡面有廟街的妓女,很多小賭檔。那裡有很多大榕樹。還有座大廟,香火很旺。「解簽,求姻緣,專騙你們這些孝女。(廟中人)用麻雀挑簽,麻雀都是經過訓練的,其實每個簽放了不同味道的米,讓麻雀跳著去選,稱『這是麻雀挑的,不是我挑的』,說是『天意』。」現在,大榕樹都砍掉,大廟變成花園。「廟街以前吃的也便宜,衣服也便宜,什麼都便宜。潮汕人做的貝殼類食物也都很好。都在那裡。現在想起來都很過癮。現在去廟街已經看不到以前香港的東西了。香港以前的天星碼頭,現在也沒有了。」「以前的小電影,色情電影,普通人看不到,要給錢,到接駁口,是個巴士。你想看黃片,就在那裡等。坐夠一車人就拉到觀塘。那個站是14K控制的。」「第一次砍人,跳上車,腦袋一片空白,太緊張。」「當時打過好多地方,控制好多地方,自己到現在都不記得了。別人說你曾經……我說我不記得了……」他說,那篇文章還想寫,「有一個幫會,在那個區域很厲害,不准其他幫會在那裡開賭檔。我曾經帶我的小弟去那裡掃掉了他們的檔口。四十多年前,我二十多歲。」三隻孝獅除了家人,司徒玉蓮在靈前哭得最多。一哭,她就立刻掏出墨鏡戴上。「要舞獅了。」有小弟特意跑來通知我們出去看。3隻黑白藍素色的獅子緩步向前,眼睛半張,鼓點和鑼聲低且輕,舞獅人跪著挪入靈堂。 2016年3月15日,香港紅勘世界殯儀館,3頭孝獅經過和鬍鬚勇一起從九江街出來的好友司徒玉蓮(左一)、陳秉寰(左二)、馬文川(綽號馬細,左三)、鄭漢義(右一)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一開始我們並不理解,這件事為什麼重要。後來聽說,上個月,另一幫會有人過世,申請舞獅,未獲警方批准。「申請……是手續,(警方)可以說不批准你在街上舞獅,當然警方肯定要有理由,阻礙交通或者什麼。但是以我所知,比如你舞白獅,你肯定要輩分很高或者很受尊重才能舞白獅,而且舞白獅時,舞一隻白獅跟舞3隻白獅是不一樣的,因為要看你這個人能不能受得起3隻白獅。」陳建國說。洪拳宗師劉家良過世時,有3隻孝獅和9隻素獅送別。「獅子不是代表是(在)社團(里)的地位。只不過是我們覺得,可能舞幾頭白獅子是對勇哥的尊重,我覺得以勇哥今時今日的地位,舞3頭白獅是不會被人笑的。」鬍鬚勇的地位,是靠「狠」奠定的。當年在九龍麻雀館睇場,鎖閉電動門,對大圈仔瓮中捉鱉,砍殺地血流成河,一戰成名。江湖人皆認其「夠膽」。有一次,陳慎芝做中間人,調停鬍鬚勇與另外一位幫派大佬的矛盾。「3個坐在這裡,勇哥一直解釋,突然那人拍桌子,勇哥說,不要再拍了。……他再拍,勇哥就站了起來(想打架)。我看到勇哥是非常冷靜的,當時外面有六七個,勇哥一個人。」鬍鬚勇的原則是有事就要立刻解決,要麼分出你死我活,要麼講和,不再糾纏。阿十見識過鬍鬚勇的不妥協。一次,鬍鬚勇被告知,他的一位做夜總會經理的小妹把一位大佬的門生懷了孕的老婆推倒在沙發上,那位大佬打上門來。小妹堅稱沒有推過人。大佬罵了她,說,不要再有下一次。鬍鬚勇不肯:這次都沒有,怎麼會有下一次。有人打圓場,說給勇哥面子,算了,沒下次就行。鬍鬚勇不依不饒:不要說下次,就講這次;就當這次推了,又怎樣?說著說著,鬍鬚勇突然起身,拉開架子。對方服軟。江湖事,江湖了。還有轟動一時的泰龍被砍殺案。「泰龍用一個啤酒瓶插了一個文身忠的脖子的動脈,傷得很厲害。如果泰龍是我的大佬,肯定不會被人砍死,肯定會跟他們談判,如果不談的話,就繼續追殺,不可以停下來。他不跟你和,一定要找你麻煩,你一定要打擊他,逼他和。這個事情不能放在一邊。」鬍鬚勇的威嚴對內也有表現。「我知道曾經有個警察,在當值的時候打了我們的人。當然可以報警或者投訴警察,但是別人打了電話來(講情)。勇哥會打給他下面的門生,說,不要投訴警察,這樣不是很好。因為他覺得如果真的因為這些小問題而產生(大麻煩),比如令那位警察因為投訴而丟了工作,他也不想。他會把事情很低調地處理。」鬍鬚勇阻止小弟投訴,只說一句話:「看醫生的錢我掏,但不准投訴。」陳建國回憶說,「我沒聽過有人問為什麼。因為他說一句必須要聽。你要問為什麼,其實沒有為什麼的。」「他心地很好的,他不會欺負人,但是你又不能惹他。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有朋友找他幫忙,他一定會幫。但是如果你不對,他就會說你不對。他是一個,我們說『行舊制』、講義氣的(人)。現在的新制,不管是跆拳道,還是別的什麼道,總之就是要有銀(錢)道,要不什麼都沒得談。」陳慎芝說。老一輩的人看不上新世道了。但鬍鬚勇這樣舊制下的人,江湖上還是賣他面子。究其原因,可能還是他的小女兒Zoe的總結:「他很著重自己的成就感,佢系一個唔衰得的人(他是一個不能失敗的人),但是他交朋友不會很看重利益方面,他是感情人,是放開利益去交朋友。」江湖流傳這樣一個故事。A花了20萬讓B去整鬍鬚勇,B一聽說是勇哥,就不答應,因為與鬍鬚勇是朋友。「很多小弟都勸我,說14K這麼多年都沒正式的盟主,為什麼你不做呢?我說如果我要做,我行強硬政策,必然會引起麻煩,但是我沒有體力去處理,就處理得不完善,倒不如有能者居之。但很可惜,感覺現在沒有誰是有能的。我覺得香港的社團,越來越不成氣候……我跟O記說,你們不想我們14K大統合,14K真的很多人的,如果我們整合,你們就會留意,就給我們麻煩,何必這樣呢?因為如果有個領導人,他們去追查,會跟著去(有跡可循);如果(組織)很散,警方就難控制。」鬍鬚勇也曾想,若退回到50歲,年富力強,沒有病痛侵擾,爭來做,也是好的。在新制下,傳統的盤踞於某塊勢力範圍深耕多年的形式已然不存在。不如適應和享受這樣的局面,不爭坐館,不那麼出頭,反而贏得更多尊重和話語權。小弟已經散開在各個角落,「就像發射站一樣,像無線電波一樣,那些電波到處去,」阿十說,「現在不是在那裡(某個地方)紮根,而是在江湖上紮根。」出殯時辰即到。11點42分,蓋棺。液晶電視里的鬍鬚勇比划著,聽不到聲音。3隻孝獅匍匐著舞到靈柩前。鬍鬚勇養的貓出現在螢幕上,瞪著眼睛,鬍鬚勇把它抱了過去。兩個畫面交錯重疊,孝獅變成了灰貓。三隻貓與三隻龜鬍鬚勇的家裡有兩隻貓。一隻叫Jack,一隻叫Lin。前者取自他以前的女朋友,後者取自熊黛林,鬍鬚勇為她不平——跟郭富城談戀愛的時候好像他的附屬品。原本還有一隻貓。趁鬍鬚勇不注意,從窗口跳了樓,砸壞了別人的車。管理處的人上樓通知鬍鬚勇賠償,要他下去看,他不肯,因正在興致勃勃地賭馬,便說,你問下車主要多少錢,我賠給他。緊接著問,那隻貓呢?管理員說,貓還沒死。鬍鬚勇趕緊跑下樓,打電話給動物協會的人來急救,自己打一輛車跟在救護車後面趕去港島的動物醫院。路上,動物協會的人打電話告訴他,貓死了。鬍鬚勇放棄追趕,讓對方幫他把貓埋了,他付錢。接著讓的士司機把車停到路邊,兩人一起賭起馬來。
2016年3月15日,香港紅勘世界殯儀館,3頭孝獅經過和鬍鬚勇一起從九江街出來的好友司徒玉蓮(左一)、陳秉寰(左二)、馬文川(綽號馬細,左三)、鄭漢義(右一)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一開始我們並不理解,這件事為什麼重要。後來聽說,上個月,另一幫會有人過世,申請舞獅,未獲警方批准。「申請……是手續,(警方)可以說不批准你在街上舞獅,當然警方肯定要有理由,阻礙交通或者什麼。但是以我所知,比如你舞白獅,你肯定要輩分很高或者很受尊重才能舞白獅,而且舞白獅時,舞一隻白獅跟舞3隻白獅是不一樣的,因為要看你這個人能不能受得起3隻白獅。」陳建國說。洪拳宗師劉家良過世時,有3隻孝獅和9隻素獅送別。「獅子不是代表是(在)社團(里)的地位。只不過是我們覺得,可能舞幾頭白獅子是對勇哥的尊重,我覺得以勇哥今時今日的地位,舞3頭白獅是不會被人笑的。」鬍鬚勇的地位,是靠「狠」奠定的。當年在九龍麻雀館睇場,鎖閉電動門,對大圈仔瓮中捉鱉,砍殺地血流成河,一戰成名。江湖人皆認其「夠膽」。有一次,陳慎芝做中間人,調停鬍鬚勇與另外一位幫派大佬的矛盾。「3個坐在這裡,勇哥一直解釋,突然那人拍桌子,勇哥說,不要再拍了。……他再拍,勇哥就站了起來(想打架)。我看到勇哥是非常冷靜的,當時外面有六七個,勇哥一個人。」鬍鬚勇的原則是有事就要立刻解決,要麼分出你死我活,要麼講和,不再糾纏。阿十見識過鬍鬚勇的不妥協。一次,鬍鬚勇被告知,他的一位做夜總會經理的小妹把一位大佬的門生懷了孕的老婆推倒在沙發上,那位大佬打上門來。小妹堅稱沒有推過人。大佬罵了她,說,不要再有下一次。鬍鬚勇不肯:這次都沒有,怎麼會有下一次。有人打圓場,說給勇哥面子,算了,沒下次就行。鬍鬚勇不依不饒:不要說下次,就講這次;就當這次推了,又怎樣?說著說著,鬍鬚勇突然起身,拉開架子。對方服軟。江湖事,江湖了。還有轟動一時的泰龍被砍殺案。「泰龍用一個啤酒瓶插了一個文身忠的脖子的動脈,傷得很厲害。如果泰龍是我的大佬,肯定不會被人砍死,肯定會跟他們談判,如果不談的話,就繼續追殺,不可以停下來。他不跟你和,一定要找你麻煩,你一定要打擊他,逼他和。這個事情不能放在一邊。」鬍鬚勇的威嚴對內也有表現。「我知道曾經有個警察,在當值的時候打了我們的人。當然可以報警或者投訴警察,但是別人打了電話來(講情)。勇哥會打給他下面的門生,說,不要投訴警察,這樣不是很好。因為他覺得如果真的因為這些小問題而產生(大麻煩),比如令那位警察因為投訴而丟了工作,他也不想。他會把事情很低調地處理。」鬍鬚勇阻止小弟投訴,只說一句話:「看醫生的錢我掏,但不准投訴。」陳建國回憶說,「我沒聽過有人問為什麼。因為他說一句必須要聽。你要問為什麼,其實沒有為什麼的。」「他心地很好的,他不會欺負人,但是你又不能惹他。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有朋友找他幫忙,他一定會幫。但是如果你不對,他就會說你不對。他是一個,我們說『行舊制』、講義氣的(人)。現在的新制,不管是跆拳道,還是別的什麼道,總之就是要有銀(錢)道,要不什麼都沒得談。」陳慎芝說。老一輩的人看不上新世道了。但鬍鬚勇這樣舊制下的人,江湖上還是賣他面子。究其原因,可能還是他的小女兒Zoe的總結:「他很著重自己的成就感,佢系一個唔衰得的人(他是一個不能失敗的人),但是他交朋友不會很看重利益方面,他是感情人,是放開利益去交朋友。」江湖流傳這樣一個故事。A花了20萬讓B去整鬍鬚勇,B一聽說是勇哥,就不答應,因為與鬍鬚勇是朋友。「很多小弟都勸我,說14K這麼多年都沒正式的盟主,為什麼你不做呢?我說如果我要做,我行強硬政策,必然會引起麻煩,但是我沒有體力去處理,就處理得不完善,倒不如有能者居之。但很可惜,感覺現在沒有誰是有能的。我覺得香港的社團,越來越不成氣候……我跟O記說,你們不想我們14K大統合,14K真的很多人的,如果我們整合,你們就會留意,就給我們麻煩,何必這樣呢?因為如果有個領導人,他們去追查,會跟著去(有跡可循);如果(組織)很散,警方就難控制。」鬍鬚勇也曾想,若退回到50歲,年富力強,沒有病痛侵擾,爭來做,也是好的。在新制下,傳統的盤踞於某塊勢力範圍深耕多年的形式已然不存在。不如適應和享受這樣的局面,不爭坐館,不那麼出頭,反而贏得更多尊重和話語權。小弟已經散開在各個角落,「就像發射站一樣,像無線電波一樣,那些電波到處去,」阿十說,「現在不是在那裡(某個地方)紮根,而是在江湖上紮根。」出殯時辰即到。11點42分,蓋棺。液晶電視里的鬍鬚勇比划著,聽不到聲音。3隻孝獅匍匐著舞到靈柩前。鬍鬚勇養的貓出現在螢幕上,瞪著眼睛,鬍鬚勇把它抱了過去。兩個畫面交錯重疊,孝獅變成了灰貓。三隻貓與三隻龜鬍鬚勇的家裡有兩隻貓。一隻叫Jack,一隻叫Lin。前者取自他以前的女朋友,後者取自熊黛林,鬍鬚勇為她不平——跟郭富城談戀愛的時候好像他的附屬品。原本還有一隻貓。趁鬍鬚勇不注意,從窗口跳了樓,砸壞了別人的車。管理處的人上樓通知鬍鬚勇賠償,要他下去看,他不肯,因正在興致勃勃地賭馬,便說,你問下車主要多少錢,我賠給他。緊接著問,那隻貓呢?管理員說,貓還沒死。鬍鬚勇趕緊跑下樓,打電話給動物協會的人來急救,自己打一輛車跟在救護車後面趕去港島的動物醫院。路上,動物協會的人打電話告訴他,貓死了。鬍鬚勇放棄追趕,讓對方幫他把貓埋了,他付錢。接著讓的士司機把車停到路邊,兩人一起賭起馬來。 2015年12月17日,香港美孚,最後陪伴鬍鬚勇抗癌的是貓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原本還有一隻狗,鬍鬚勇嫌它粘人,送給了女兒。這個家是如此匹配兩隻高冷的貓。玄關處5雙黑皮鞋一字排開,沒有準備任何的客用拖鞋。鞋櫃里是十幾雙幾乎嶄新的鞋,全黑。走廊盡頭掛著一把劍,是一位香港高級警官去德國深造時,德國警察送他的禮物,港警把它轉送給了鬍鬚勇。司徒玉蓮幫他收拾屋子的時候,從一堆禮物里把劍挑了出來,掛置在牆上,「掛起來像不像十字架?我覺得那十字架保佑了他十幾年,他還不相信。」司徒玉蓮是基督徒,2012年在以色列受洗。「我決志(信仰耶穌)差不多二十年,但是我對自己的要求蠻高的,因為我還在社會裡,後來我才明白在信仰里,上主不一定要我們乾乾淨淨的,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不幹凈的。」她相信鬍鬚勇有一天會入主。因為少年時在教會學校念書,鬍鬚勇背聖經比司徒玉蓮還溜,但堅稱自己「無神論」。他手上戴一串佛珠,是乾兒子的心意。伍霆峰在得知他患病後也於白眉派宗堂前為他點長壽香。小女兒覺得徹夜的祈禱曾在危難關頭助父親挺過,也成了基督徒。即便不拜不信仰,循例,鬍鬚勇家裡也應該擺著穿黑鞋的關公像。問他,他很尷尬地指指牆角的一方空木框,說,以前擺在那裡,「爛了,跌下來爛了。被貓弄破了……我又病,沒時間安返去(補回來)……」鬍鬚勇想抱一下Jack,趕到臥室里的洗手間門口,彎腰,沒抱到。J跳到桌上,穿過桌面,跳下,鬍鬚勇俯身再抱,又落空。J跳上電視桌,鑽到電視機後面,跑下來,上了床頭櫃,鬍鬚勇剛一哈腰,J又竄到桌子下,躲進洗手間。鬍鬚勇把它堵在馬桶旁,一陣器皿碰撞的聲音後,J終於被按住,抱起。但它迅速咬了他一口,逃走了。有一瞬間,他的眼神凶起來,帶著怒氣。轉而想法破解丟臉的尷尬。他至少說了四遍:它怕我抱走,以前都可以抱的。臥室的書架上擺著門類雜亂的書:《成人英語課程》、《標準英漢詞典》、《牛津英漢詞典》、《英文同音詞手冊》、《圖解詠春拳——李小龍校正》、《輕渡癌關》、《熱帶魚水草養殖法》、《刑罰的歷》、《性病新知》、《圖解台灣史》、《宋詞名句欣賞》、《現代汽車的結構與維修》、(書頁老舊的)《新歌集new song book》、《看圖例學window7》。採訪時,兩隻貓輪番來打擾,鬍鬚勇會在嚴肅地講述幫會儀式、血腥拼殺或者別的什麼性命攸關的時刻,突然話鋒轉柔:「Lin,你想點啊(你想怎麼樣啊),走來搞搞震你不怕丑(害羞)嗎?好啦,抱一下下。」然後用粗重的力道迅速為貓通身按摩幾下。他還養過兩隻金錢龜一隻草龜。野生金錢龜是小弟送的,聽說可以解毒治病,他給養大了便不捨得吃,病友聽說他有,想高價買,他都不肯。草龜是花一二百塊錢買的,爪子受了傷,獸醫看過,要了萬把塊錢治病。鬍鬚勇臨終入院前,草龜失蹤了幾個月。後來他女兒收拾衣櫃,發現龜不知怎麼鑽進去的,還爬上了層層櫃檯,疊在一摞衣服里。發現時,已經腐化成一層殼了。至今,這副殼還躺在鬍鬚勇的衣櫃里,沒人敢動它。一家人鬍鬚勇本可以不這麼孤獨。Zoe曾與他同住照顧,但後來他還是讓女兒回去自己的家。他還是喜歡獨自一人生活,也不用擔心自己的病痛干擾到別人。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他便與他們疏離,有時一年才見一次面。
2015年12月17日,香港美孚,最後陪伴鬍鬚勇抗癌的是貓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原本還有一隻狗,鬍鬚勇嫌它粘人,送給了女兒。這個家是如此匹配兩隻高冷的貓。玄關處5雙黑皮鞋一字排開,沒有準備任何的客用拖鞋。鞋櫃里是十幾雙幾乎嶄新的鞋,全黑。走廊盡頭掛著一把劍,是一位香港高級警官去德國深造時,德國警察送他的禮物,港警把它轉送給了鬍鬚勇。司徒玉蓮幫他收拾屋子的時候,從一堆禮物里把劍挑了出來,掛置在牆上,「掛起來像不像十字架?我覺得那十字架保佑了他十幾年,他還不相信。」司徒玉蓮是基督徒,2012年在以色列受洗。「我決志(信仰耶穌)差不多二十年,但是我對自己的要求蠻高的,因為我還在社會裡,後來我才明白在信仰里,上主不一定要我們乾乾淨淨的,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不幹凈的。」她相信鬍鬚勇有一天會入主。因為少年時在教會學校念書,鬍鬚勇背聖經比司徒玉蓮還溜,但堅稱自己「無神論」。他手上戴一串佛珠,是乾兒子的心意。伍霆峰在得知他患病後也於白眉派宗堂前為他點長壽香。小女兒覺得徹夜的祈禱曾在危難關頭助父親挺過,也成了基督徒。即便不拜不信仰,循例,鬍鬚勇家裡也應該擺著穿黑鞋的關公像。問他,他很尷尬地指指牆角的一方空木框,說,以前擺在那裡,「爛了,跌下來爛了。被貓弄破了……我又病,沒時間安返去(補回來)……」鬍鬚勇想抱一下Jack,趕到臥室里的洗手間門口,彎腰,沒抱到。J跳到桌上,穿過桌面,跳下,鬍鬚勇俯身再抱,又落空。J跳上電視桌,鑽到電視機後面,跑下來,上了床頭櫃,鬍鬚勇剛一哈腰,J又竄到桌子下,躲進洗手間。鬍鬚勇把它堵在馬桶旁,一陣器皿碰撞的聲音後,J終於被按住,抱起。但它迅速咬了他一口,逃走了。有一瞬間,他的眼神凶起來,帶著怒氣。轉而想法破解丟臉的尷尬。他至少說了四遍:它怕我抱走,以前都可以抱的。臥室的書架上擺著門類雜亂的書:《成人英語課程》、《標準英漢詞典》、《牛津英漢詞典》、《英文同音詞手冊》、《圖解詠春拳——李小龍校正》、《輕渡癌關》、《熱帶魚水草養殖法》、《刑罰的歷》、《性病新知》、《圖解台灣史》、《宋詞名句欣賞》、《現代汽車的結構與維修》、(書頁老舊的)《新歌集new song book》、《看圖例學window7》。採訪時,兩隻貓輪番來打擾,鬍鬚勇會在嚴肅地講述幫會儀式、血腥拼殺或者別的什麼性命攸關的時刻,突然話鋒轉柔:「Lin,你想點啊(你想怎麼樣啊),走來搞搞震你不怕丑(害羞)嗎?好啦,抱一下下。」然後用粗重的力道迅速為貓通身按摩幾下。他還養過兩隻金錢龜一隻草龜。野生金錢龜是小弟送的,聽說可以解毒治病,他給養大了便不捨得吃,病友聽說他有,想高價買,他都不肯。草龜是花一二百塊錢買的,爪子受了傷,獸醫看過,要了萬把塊錢治病。鬍鬚勇臨終入院前,草龜失蹤了幾個月。後來他女兒收拾衣櫃,發現龜不知怎麼鑽進去的,還爬上了層層櫃檯,疊在一摞衣服里。發現時,已經腐化成一層殼了。至今,這副殼還躺在鬍鬚勇的衣櫃里,沒人敢動它。一家人鬍鬚勇本可以不這麼孤獨。Zoe曾與他同住照顧,但後來他還是讓女兒回去自己的家。他還是喜歡獨自一人生活,也不用擔心自己的病痛干擾到別人。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他便與他們疏離,有時一年才見一次面。 2016年2月16日,香港荃灣港安醫院,大兒子潘少傑在給昏迷中的鬍鬚勇按摩浮腫的手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不知道幾歲時,大兒子潘少傑生日,鬍鬚勇突然拎著一個蛋糕和一個龍蝦沙拉出現在孩子面前。少傑很開心,但又覺得「有點恐懼」,他的樣子「好兇」。他知道爸爸是做偏門的。不到10歲時,有一次潘少傑發燒,爸爸打車帶他看醫生,的士司機故意兜路,爸爸拿起石頭打破了擋風玻璃,然後拉著他躲進了麻將館。「我覺得他是最難面對家人,有點逃避家庭。」潘少傑說。長大後他也曾跟父親同住過一段時間,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每天的對話只是他叫一聲「爸」,然後兩人各自回屋。「我以前很怪我爸,覺得他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生活,到長大了才明白他是不想我們沾染他(圈子)的東西。」Zoe說。鬍鬚勇坐過半年牢,那期間,Zoe給他寫信,傾訴自己的想法。一直忙碌、逃避的鬍鬚勇開始回信解答。在婚戀年齡,Zoe交了男朋友Andy,在賭場工作。鬍鬚勇知道後很反對,他見到Andy的第一句話是,「玩歸玩,但是一定要回家睡覺。」鬍鬚勇希望子女們能夠好好讀書,不要像他那樣。但他並不知道怎樣將這個願望實現。最終,在他的惡疾面前,一家人開始和解和彼此接受。在鬍鬚勇最後的時光里,兒女們輪流陪在他身旁。成家後明白了家庭的複雜,潘少傑覺得自己能夠諒解父親了。在病房裡,他幫父親擦拭,第一次摸到父親的手,才感到,原來父親是這樣的啊,「終於感覺到跟爸爸很接近」。兩人還能一起看電視,聊聊電視的內容,而又剛好,電視正在播放電視劇《愛·回家》想想,還感覺有點不可思議。相較於子女,鬍鬚勇跟弟弟阿十更親近。我問阿十,為什麼選擇了跟哥哥一樣的生活方式,他說,「其實不需要選擇,十幾歲就跟他一起工作,大家的生活方式都融入了,都沒考慮做什麼,他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所以不用重新選擇。」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潘志泉對潘志勇的稱呼,由按照排名來的「八哥」,變成了「大佬」,很少再叫哥。但阿十不想做鬍鬚勇那樣的大佬,「他一天背著八九張擔保紙,整天去見警察,整天去跟人講數,處理小弟發生的糾紛。我覺得很辛苦,但是他不一定會覺得辛苦,就像明天要上堂,今天先去打麻將。(我們的能力和承受力是)不同的。」在最後的病房,黑道大佬鬍鬚勇的周邊終於有了些家的樣子。他身上蓋著五顏六色的花格子毛毯,米老鼠唐老鴨的脖枕,窗台上陳列著一隻輕鬆熊,牆上貼的、門上掛的是史迪奇和Hello Kitty的祝符,還有卡通化了的一家幾口簇擁著4個字:家肥屋潤。「如果我往生之後,我當然希望家人平安,不需要大富大貴,生活無慮會更好。幫會方面我當然希望能發展好一點,最重要是不要留臭名。我有個原則,有些事情犯法無可避免,但是要儘量對人公平,不要太傷天害理。」即便沒有了他,香港的幫會還會照常運轉,「香港黑社會其實不是野心太大,他能賺錢就不會亂的,香港黑社會跟外國的相比已經是比較平和的了,香港受控制的程度比外國要加重一點的。」鬍鬚勇心裡清楚,傳統幫派已經流逝得殘渣無幾。「現在很多幫派,連大哥都不懂這些東西,我們以前早上吃東西,筷子要擺成『卜』字,中午也是,晚(上)要擺『旦』……香港的大哥十個有九個不懂。我很少跟人講的,這是第一次。以前如果遞筷子給你,遞三根是你怎麼吃(飯),那你就呆了,如果你會說,就說,『洪門結義留關張,義兄拿單我拿雙』,有這些規矩的。……現在沒人懂了,很多黑社會元老都不懂,現在聊起來像故事一樣,很好笑。」鬍鬚勇唏噓,「社會越來越進步,黑社會在進步,現在為什麼沒有入會儀式,因為有很多人當了線人,一搞就容易被警察全都抓了,就慢慢轉化從簡。……現在都是給封利是就可以,現在的轉變是因為社會進步了,現在吟詩作對沒用了,最重要是實力,人們是現實了。」這三四十年前就開始起的變化,如今只留下歷史的背影。「打架,一定是打錢的,以前黑社會是為了錢,現在已經沒有那個必要去打一場大架了……」陳建國說。在葵涌火葬場,眾人最後一次給鬍鬚勇上香。陳慎芝兩次拒絕了別人遞給他的燃香,「因為信主。」茅躉華退到人群後面。吳警官經過時跟他打了招呼。「警察都對我很好的。他們知道我是什麼人。」吳警官開車離開後,茅躉華進入一號禮堂,拍照留念。陳秉寰看上去跟在殯儀館時的樣子有些不同,神情緩和,凶態消失了。他拄著拐杖,抽了一支煙,像個尋常的市井老人。葬禮馬上結束。一直跟拍視頻的工作人員設計了這樣一幕,眾人對著空中盤旋的航拍器揮手,大聲道:「勇哥,走好!」就這樣,拍了三條。工作人員一句OK,人群散去。大佬的這部電影,落幕了。(感謝凌江嬋整理錄音)本刊記者|張蕾 方迎忠 封面攝影|方迎忠 發自香港編輯|張歡 [email protected]
2016年2月16日,香港荃灣港安醫院,大兒子潘少傑在給昏迷中的鬍鬚勇按摩浮腫的手 圖/本刊記者 方迎忠不知道幾歲時,大兒子潘少傑生日,鬍鬚勇突然拎著一個蛋糕和一個龍蝦沙拉出現在孩子面前。少傑很開心,但又覺得「有點恐懼」,他的樣子「好兇」。他知道爸爸是做偏門的。不到10歲時,有一次潘少傑發燒,爸爸打車帶他看醫生,的士司機故意兜路,爸爸拿起石頭打破了擋風玻璃,然後拉著他躲進了麻將館。「我覺得他是最難面對家人,有點逃避家庭。」潘少傑說。長大後他也曾跟父親同住過一段時間,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每天的對話只是他叫一聲「爸」,然後兩人各自回屋。「我以前很怪我爸,覺得他為什麼不跟我們一起生活,到長大了才明白他是不想我們沾染他(圈子)的東西。」Zoe說。鬍鬚勇坐過半年牢,那期間,Zoe給他寫信,傾訴自己的想法。一直忙碌、逃避的鬍鬚勇開始回信解答。在婚戀年齡,Zoe交了男朋友Andy,在賭場工作。鬍鬚勇知道後很反對,他見到Andy的第一句話是,「玩歸玩,但是一定要回家睡覺。」鬍鬚勇希望子女們能夠好好讀書,不要像他那樣。但他並不知道怎樣將這個願望實現。最終,在他的惡疾面前,一家人開始和解和彼此接受。在鬍鬚勇最後的時光里,兒女們輪流陪在他身旁。成家後明白了家庭的複雜,潘少傑覺得自己能夠諒解父親了。在病房裡,他幫父親擦拭,第一次摸到父親的手,才感到,原來父親是這樣的啊,「終於感覺到跟爸爸很接近」。兩人還能一起看電視,聊聊電視的內容,而又剛好,電視正在播放電視劇《愛·回家》想想,還感覺有點不可思議。相較於子女,鬍鬚勇跟弟弟阿十更親近。我問阿十,為什麼選擇了跟哥哥一樣的生活方式,他說,「其實不需要選擇,十幾歲就跟他一起工作,大家的生活方式都融入了,都沒考慮做什麼,他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所以不用重新選擇。」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潘志泉對潘志勇的稱呼,由按照排名來的「八哥」,變成了「大佬」,很少再叫哥。但阿十不想做鬍鬚勇那樣的大佬,「他一天背著八九張擔保紙,整天去見警察,整天去跟人講數,處理小弟發生的糾紛。我覺得很辛苦,但是他不一定會覺得辛苦,就像明天要上堂,今天先去打麻將。(我們的能力和承受力是)不同的。」在最後的病房,黑道大佬鬍鬚勇的周邊終於有了些家的樣子。他身上蓋著五顏六色的花格子毛毯,米老鼠唐老鴨的脖枕,窗台上陳列著一隻輕鬆熊,牆上貼的、門上掛的是史迪奇和Hello Kitty的祝符,還有卡通化了的一家幾口簇擁著4個字:家肥屋潤。「如果我往生之後,我當然希望家人平安,不需要大富大貴,生活無慮會更好。幫會方面我當然希望能發展好一點,最重要是不要留臭名。我有個原則,有些事情犯法無可避免,但是要儘量對人公平,不要太傷天害理。」即便沒有了他,香港的幫會還會照常運轉,「香港黑社會其實不是野心太大,他能賺錢就不會亂的,香港黑社會跟外國的相比已經是比較平和的了,香港受控制的程度比外國要加重一點的。」鬍鬚勇心裡清楚,傳統幫派已經流逝得殘渣無幾。「現在很多幫派,連大哥都不懂這些東西,我們以前早上吃東西,筷子要擺成『卜』字,中午也是,晚(上)要擺『旦』……香港的大哥十個有九個不懂。我很少跟人講的,這是第一次。以前如果遞筷子給你,遞三根是你怎麼吃(飯),那你就呆了,如果你會說,就說,『洪門結義留關張,義兄拿單我拿雙』,有這些規矩的。……現在沒人懂了,很多黑社會元老都不懂,現在聊起來像故事一樣,很好笑。」鬍鬚勇唏噓,「社會越來越進步,黑社會在進步,現在為什麼沒有入會儀式,因為有很多人當了線人,一搞就容易被警察全都抓了,就慢慢轉化從簡。……現在都是給封利是就可以,現在的轉變是因為社會進步了,現在吟詩作對沒用了,最重要是實力,人們是現實了。」這三四十年前就開始起的變化,如今只留下歷史的背影。「打架,一定是打錢的,以前黑社會是為了錢,現在已經沒有那個必要去打一場大架了……」陳建國說。在葵涌火葬場,眾人最後一次給鬍鬚勇上香。陳慎芝兩次拒絕了別人遞給他的燃香,「因為信主。」茅躉華退到人群後面。吳警官經過時跟他打了招呼。「警察都對我很好的。他們知道我是什麼人。」吳警官開車離開後,茅躉華進入一號禮堂,拍照留念。陳秉寰看上去跟在殯儀館時的樣子有些不同,神情緩和,凶態消失了。他拄著拐杖,抽了一支煙,像個尋常的市井老人。葬禮馬上結束。一直跟拍視頻的工作人員設計了這樣一幕,眾人對著空中盤旋的航拍器揮手,大聲道:「勇哥,走好!」就這樣,拍了三條。工作人員一句OK,人群散去。大佬的這部電影,落幕了。(感謝凌江嬋整理錄音)本刊記者|張蕾 方迎忠 封面攝影|方迎忠 發自香港編輯|張歡 [email protected]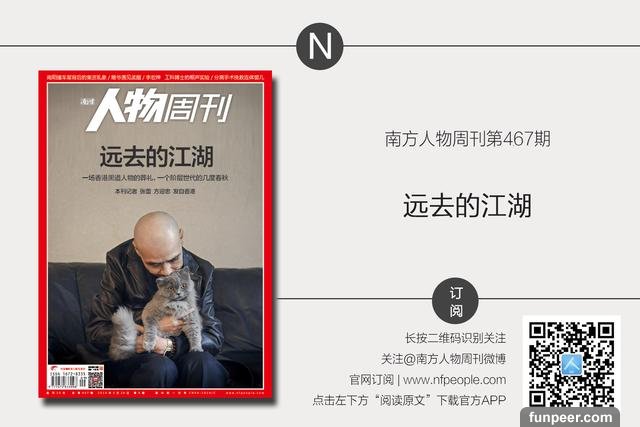
[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
|
本篇 |
不想錯過? 請追蹤FB專頁! |
| 喜歡這篇嗎?快分享吧! |
相關文章
今日大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