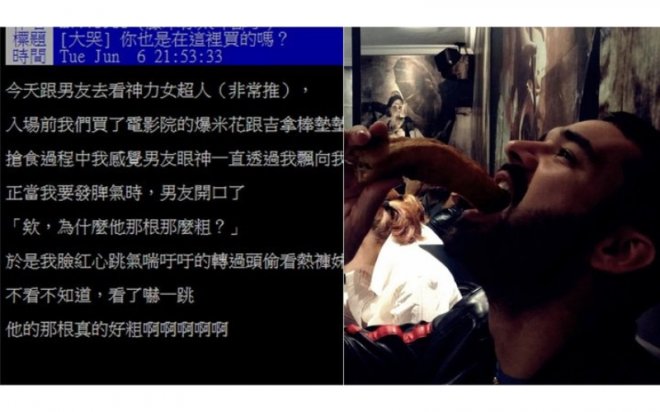哈利波特竟變成會放屁的「多功能屍體」,很多人看到1分10秒的地方,就超WTF看不下去了

(圖片翻攝自好奇心日報 )
一週前,我們才下飛機一個小時,就坐在了猶他州帕克市的埃克爾斯劇院(Eccles Theater)裡,觀看《瑞士軍人》(Swiss Army Man)在今年聖丹斯電影節的全球首映。觀眾們不知道會看到什麼,甚至到現在也解釋不清楚。最終上演的其實是部高級黑色喜劇,雖然偶爾會轉向廁所幽默——但影片所有內容都指向了孤獨、渴望和羞恥這些實實在在的主題。許多討論圍繞著丹尼爾‧雷德克裡夫扮演的放屁殭屍角色,或是保羅‧達諾著了魔的表演,而完全抓住我們注意力的,是這部影片的音效設計。導演雙人組 Daniels (Daniel Scheinert 和 Daniel Kwan) 以及音效設計師 Brent Kiser 向我們解釋了他們如何搭建聲音景觀:從氣體噴發到出人意料的音樂劇曲目。

(圖片翻攝自好奇心日報 )
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或許是,不管角色是死是活,都會忽然唱起歌來。這部影片不是音樂劇,卻包含有音樂劇的曲目——採用角色本來的聲音,編織成音符。Kwan 解釋說:「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是部很主觀的影片,因為大部分內容來自一個男人的視角。我們從這裡著手,音樂立意來自他的聲音、想法,還有不同層面的心聲。我們想讓觀眾感覺,你就在他腦袋裡。你感到他所感受的喜悅、痛苦,還有迷惑。」Scheinert 補充說:「一旦我們有了敘事的節奏,他要開始重現記憶,搭建場景了,我們就說,『哦,他應該發出聲音。他要唱出來!我們把他的音效做出來吧。』」
人人都唱歌,多數人唱歌時覺得尷尬。人人都放屁,多數人放屁時也覺得尷尬。
「歌聲與屁聲有可比性。這就像事物的陰陽兩面,都是由身體產生的真實、純粹的聲音。人人都唱歌,多數人唱歌時覺得尷尬。人人都放屁,多數人放屁時也覺得尷尬。」Kwan 說:「我們不喜歡無伴奏的音樂。伴奏是樂趣的一部分。」Andy Hull 和 Robert McDowell 是曼徹斯特管絃樂團的兩位樂隊成員,他們花了 11 個月時間為電影配樂。Kiser 解釋說:「許多聲音是從音效做成音樂的,導演要在現場播放錄音,演員對口型。而且我們很多次在音樂的開頭和結尾用了製作音頻片段。」這些錯綜複雜的聲音把觀眾包圍了起來。

(圖片翻攝自好奇心日報 )
兩個人都提到,音樂在製作過程中,和觀眾起的作用差不多。在片場,演員們會主動要求聽歌。Scheinert 說:「目的是通過聽聲音,在情緒上把握這種危險變態的內容,給我們機會來說:『不不不,這其實挺美的。』這是一部關於美和用美來對抗羞恥的電影。」最令人難忘的歌是關於爆米花的:「我們有些歌詞就是在直白地描述人們螢幕上看到的畫面,這是最誠實、簡單的歌唱方式,」Kwan 解釋說,「歌詞是『爆爆米花,爆爆米花』,特別傻,但是在影片中,角色們有了爆米花非常激動。不害臊地唱起歌來是很美的。」Kwan 解釋說,脫口而出的歌詞就是人們大腦的入口。不過音樂劇過於誠懇了。另外,Scheinert 很喜歡的是,這部電影中「忽然唱起來這種古怪的做法有其敘事的價值。角色忽然唱起歌來,是因為他已經孤獨太久了。」
首先,我們做了個 6 小時長的放屁錄音,於是工作人員有了足夠多聲音素材做編輯,隨意表達想法,帶著感情運用這些屁聲——否則就只有喜劇效果了。
胃腸脹氣在引入角色和展現角色潛力方面,發揮著很大作用。Kiser 指出:「首先,我們做了個 6 小時長的放屁錄音,於是工作人員有了足夠多聲音素材做編輯,隨意表達想法,帶著感情運用這些屁聲——否則就只有喜劇效果了。我們不想做成卡通片。」 Scheinert 說,「我們還從 YouTube 上偷了一些放屁聲,上面有人錄下了自己真實的放屁聲。」後來 Kiser 在工作室對這些內容進行了在創作。(他補充說:「我們還沒接到來自 YouTube 那些人的電話,比如,「順便說一聲,我在 Shazam 發表了這個屁聲,版權屬於我,我要收你一百萬美元。」)兩位導演都意識到,許多人不喜歡放屁的笑話;他們自己也不喜歡。謹記這點,「我們算是故意地快速播出屁聲,然後停下。電影中大部分的屁聲都沒有持續。屁被堵住了。」 Scheinert 說。
「因為我們把笑點一帶而過,所以說真實性才是關鍵,還有身體的姿勢。我們想要一個感覺忠實於畫面的聲音,讓你覺得這是玩笑,你會思考這個姿態,或者想,他是不是難過了,哪兒有水,」 Kwan 說,「我們想讓觀眾自己形成對放屁的看法,幫助人們放下偏見,不僅是對放屁這件事,還有使人們感到羞恥的所有事。人們覺得不能向別人展示的所有東西。」而這依然需要簡單的幽默,需要呈現給觀眾,使他們同時對角色更深入地理解。

(圖片翻攝自好奇心日報 )
另一個反覆出現的音樂手法是《侏儸紀公園》的主題歌。Daniels 解釋說,這首歌有敘事的價值,同時又承認,他們自己經常會唱——尤其是在推廣項目的時候。「我們認為,如果整部片子裡都是歌,卻沒有你腦中迴蕩的那些歌,這是不坦誠的。加入片中百分之百是原創音樂,就會感覺缺少那種共鳴——比如,我們都知道 Cross fire 的廣告歌,」Scheinert 說。Kwan 補充說:「尤其當你想講段故事,不管講什麼,因為某種原因你唱出了《侏儸紀公園》,Daniel 滿腦子都是《侏儸紀公園》。我們覺得,這樣很好玩。」除了這個關鍵因素以外,John Williams 這段配樂並沒有把兩個孤立的角色留在多數人熟悉的世界裡。
Daniels 在製作音樂錄影帶方面有非常成功的經歷。這在他們的影片製作、乃至最終成片的基調、節奏方面都有所體現。Scheinert 解釋說:「我們是兩個導演,想要像一個導演那樣思考。很多人問:『你們怎麼把不同的想法結合起來,做出有凝聚力的東西?』音樂就是很好的橋樑,因為,本質上音樂就是種翻譯。因為我們有兩個大腦,音樂是聯結我們想法的關鍵。」在整部電影中,音樂都以非同尋常、不乏共鳴的方式潛入了觀眾的腦中。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影片所傳達信息與經驗的一個比喻。
相關文章
最hot趣味話題